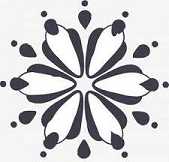先秦两汉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与心性论,也是魏晋玄学兴起的重要原因
发布时间:2024-04-02 03:29:30作者:楞伽经讲什么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追溯至商代的占卜。《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表明,远古时代的人们似乎以为,在人的主观意志以外,存在着某种支配和影响现实社会生活的东西,它决定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社会行动。只不过由于认识水平所限,殷人将这种具有客观必然意义的存在理解为“帝”,并将其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于是,殷人几乎每事必卜。
商代频繁发生的占卜行为,实际上是在认识能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把握客观必然性所做的努力。西周初期人们不再使用商代“帝”的概念,而更多使用“天”的概念,从此“天”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概念。西周时期的人们把“天”看做是万物以及人的来源,周宣王时的尹吉甫作《烝民》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里已含有人民的德性来自“天”的含义。
西周时期的“天”明显带有某种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种人为“神之主”的观点。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郑国子产更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这种强调人的重要性的思想观念,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人是天人关系中的主体。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战国儒家的思孟学派那里臻于成熟,这一观念为汉代春秋公羊学所继承下来,其具体表现形式便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正确地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原因不是人本身,而是作为客观必然性的天,“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
同时,董仲舒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也应该通过“天”来说明,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但是,由于形而上学修养的相对欠缺,董仲舒无法在天人之间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因此,他只能用简单比附的方式来说明天人合一这一论题。结果,汉代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流于神秘化与庸俗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魏晋玄学兴起的重要原因。
宋代理学家继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北宋前期的张载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论题。他在《正蒙·乾称篇下》中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中也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学际天人也就是通贯天人,对天人关系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宋代理学家认为,天就是理。由于理是二程以后理学的核心范畴,所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便成为思想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宋代理学家所理解的天,已经不再是汉儒所说的那种具有人格特征,可以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实行赏罚的天,而更多的是必然性意义上的天。宋儒坚持天人合一的论题,其主观目的是要说明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与普遍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天、性、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所以朱熹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宋儒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显然远远超过了汉唐儒家的理解水平。
正是由于对天人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宋代理学家才能够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把握天理,并且在天理与现实的政治生活之间建立起内在的逻辑联系。当宋代理学家在抽象的水平上理解了天人关系的时候,天或天理成为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也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作为认识主体,人的心性修养的重要性便日益显现出来,因为作为客观存在的天或天理是需要人来认识的,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也必须具有与天理相适应的道德品质。由于这一原因,宋代理学家尤其重视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
先秦儒家特别是儒家的思孟学派,尤其重视人的心性修养。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保存了一些先秦儒家有关心性问题的材料。据说,这些材料体现了子思学派的思想。其中,《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性之于人是一种普遍的共性。子思学派谈人性,主要是指人的心理特性。《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
在子思学派的思想体系中,仁、义、礼、智是外加于心的美德。人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的言谈举止体现出德行,只有将德行内化于心,方能成为君子:“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
孟子继承了子思的心性论,并且赋予了心与性清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心性论体系。在孟子看来,所谓心就是仁、义、礼、智之本心,这种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人人都有这“四心”,这是人的“本心”。
孟子把心理解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同时,他也强调“心”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认识功能:“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孟子认为,就本性而言,人与动物的差别极其细微,“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而“心”正是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心”。人之所以能够具有异于禽兽的品质,就在于人类具有道德的本心和认识能力。因此,孟子强调要尽心、知性进而知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两宋理学家更多地接受了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天或者天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心性修养便是达到天理的先决条件。
如北宋时期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便十分重视“养心”:“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一方面,他认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圣,诚而已矣”。
周敦颐这段话代表了两宋时期理学家的普遍认识。两宋理学家一方面断定,天理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把个人的心性修养作为达到天理进而实践普遍道德法则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