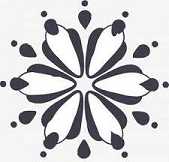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发布时间:2022-10-03 09:09:41作者:楞伽经讲什么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高振农
一、玄奘一生的弘法活动
玄奘是中国着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其毕生的弘法活动,先是西行求法,后是翻译佛典。
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万里,所闻所履138国。他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的当时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俱舍论》、《大毗婆娑论》、《因明》、《声明》等论典,重点钻研了《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前后五年,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备受礼遇,其名声仅次于戒贤。后又历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进行广泛参学,凡4年。回到那烂陀寺后,即应戒贤之嘱,主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并会通大乘佛教中“中观”、“瑜伽”两派的争论,撰《会宗论》三千颂,得戒贤等人赞许。又应戒日王请,着《制恶见论》,驳斥正量部论师般若?NFD54?多的《破大乘论》。戒日王还为他在曲女城设大法会,十八天中无人能破其论点,被称为“解脱天”和“大乘天”。回国时带回梵文经典(包括大小乘佛教经、律、论)520夹,计657部。
他回国后主要从事翻译佛典。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夏开始,至麟德元年(664年)初为止,近二十年间,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他是中国唐代译经者中译经最多的一人,所译经论,约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译经的一倍多。他所译的经论,由于质量较高,后人称之为新译。
玄奘在印度所撰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都没有能流传下来。属于他自己的着述,有四章十二颂四十八句的《八识规矩颂》,主要讲唯识学说中心的心识问题,但没有单行本,靠注释本流传。其他就是由他口述,其弟子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这部着作在中国佛教着作中很有名,影响亦很大,但它只是一部佛教史籍,不是一部阐述佛教理论的着作。从这一意义上说,玄奘自己撰写的阐发佛学思想的着作,流传下来的很少。
玄奘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阐发佛学思想的着述,但他所翻译、流传的佛教经论,却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
玄奘一生,花了数十年的精力,系统地翻译了印度的戒贤所传的瑜伽行派的唯识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自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人们的意识变现出来的,即所谓“唯识所变”。因而提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理论。认为最根本的意识是“阿赖耶识”,是世界各种事物、现象的“种子”,是宇宙的本原。一切事物、现象都由“阿赖耶识”所派生。同时,玄奘还进一步发挥了印度戒贤一系的五种姓说,认为声闻种姓、独觉种姓、菩萨种姓具有先天的决定根性,定能成道。不决定根性,能否得道还不能一定。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入道。正是由于这些理论,从而开创了具有特色的唯识宗。
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可说是忠实地继承了印度瑜伽行派戒贤一系的学说。吕澂先生曾经说过:“公正地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这是一种正确的评价。
二、玄奘学说的衰微及其主要原因
玄奘所传印度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说,由于忠实地保持了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在唐代曾盛极一时。但是,它在数传以后即趋向衰微,其原因是什么?有人提出,因为这种学说,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理论,虽有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但却非常繁琐,故不受人们的欢迎,数传即衰。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首先,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已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许多高僧大德、佛教学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翻译佛典和注释佛典,而是热衷于独立撰写佛学着作,进一步发挥佛教义理,从而使佛教逐步走向中国化。
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由于已和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而很快为人们所接受。相反,忠实于印度佛学的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则因为与中国传统思想差距太大,不为人们所欣赏,因而逐渐被湮没。这可说是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所以在数传以后即衰落的原因之一。
其次,玄奘所传唯识理论所以在数传后即衰微,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大家知道,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佛性”问题曾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这一理论和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学佛修佛,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成佛。
早在北凉昙无谶译出40卷本《大般涅〖FJF〗?NB231?〖FJJ〗经》之前,鸠摩罗什的弟子道生在阐发涅〖FJF〗?NB231?〖FJJ〗理论时,就孤明先发,首唱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即主张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一阐提也不例外。40卷本《大般涅〖FJF〗?NB231?〖FJJ〗经》译出流行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的思想,更是流行一时。在隋唐时期先后成立的各个佛教宗派,有许多是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的。例如:
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根据般若空观,主张“理”为佛性,亦即以“中道”。为佛性,认为凡是能体证到中道的正智(般若)者,都有成佛的可能。
天台宗从善恶方面讲佛性,认为佛和“一阐提”的心中,都是善恶染净无所不具的,因此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天台宗九祖湛然为了反对华严宗只承认有情(一切有情识的生物)有佛性的说法,特作《金刚?NFD53?》,宣扬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也有佛性的主张,认为无情之物也能成佛。
华严宗四祖澄观,吸取了天台宗的观点,主张佛和众生都有性善、性恶两方面,因此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但只是承认有情有佛性,反对无情识的生物也有佛性。
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主张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在他看来,佛性就是恒常清净的真如本性,也就是人的本心、本性。人人都有恒常清净的佛性,人人的本心都具菩提的智慧,包含有诸佛和佛理,因此一切众生的佛性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人们一旦认识本心,就能豁然顿悟而解脱成佛。同时还认为佛性是派生万事万物的清净的精神实体,一切现象都包含在自性之中。
从上可以看出,隋唐时期成立的一些佛教宗派中,三论、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都是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在这种形势下,玄奘一系的法相宗,仍坚持其五种姓说,主张有一种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成佛。这些说法,不仅与当时大多数人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的思想背道而驰,而且也得不到广大佛教徒的支持与拥护。这是由于,佛性问题,即一切众生是否都有佛性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佛学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修行实践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佛教徒,他们学佛、修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解脱,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成佛。如果有一种人,毕竟不能成佛,那人们修行学佛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认为,法相宗之所以在唐代盛极一时,数传以后即趋向衰落,最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这与玄奘及其弟子辈坚持五种姓说有很大的关系。
三、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及其原因
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之学,数传以后即趋向衰落,除了以上所说的其理论本身比较繁琐,以及五种姓说不受佛教徒欢迎等原因外,还有因为经过唐武宗的灭佛及五代的战乱,有关研究法相唯识之学的疏记,散失殆尽,人们无法对之进行研究。因此,从元末到明初,研究唯识之学的,可说已绝其迹。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朝初年,虽有一些唯识研究家出现,但由于没有嫡传玄奘之学的窥基等疏记作为依据,因而总是不得入门。有人苦心积虑想直接从《成唯识论》着手研究,而结果仍然不得要领,在许多地方失其正义。因此可以这样说,宋元以来,直至明末清初,玄奘所传唯识之学,一直处于衰微状态。
但是,到了近代,却出现新的转机,呈现出复兴的迹象。有人运用法相唯识的理论,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在整理中国传统思想时借鉴了法相唯识学中细致的名相分析方法。一时间,许多人竞相研习法相唯识学,或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研究;或创办佛教大学等学习机构,培养专门人才;或着书立说加以弘扬,可谓盛极一时。与此同时,与弘扬法相唯识学有关的佛教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普遍兴起。从此,玄奘所传的唯识思想,重新得到流行,并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一)复兴的主要标志
唐代法相唯识学的弘传与盛行,主要表现在玄奘翻译了大量的法相唯识典籍以及其弟子辈的竞作注疏。如玄奘先后翻译了《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解深密经》、《显扬圣教论》、《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杂集论》、《辨中边论》、《大乘五蕴论》、《成唯识论》等。此外,还翻译了与唯识理论有关的因明着作《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等。其弟子窥基撰有《成唯识论述记》、《辨中边论述记》、《二十唯识论述己》、《瑜伽师地论略纂》、《杂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因明入正理论疏》等。窥基的弟子慧沼撰有《成唯识论了义灯》、《能显中边慧日论》、《因明入正理义纂要》等。慧沼的弟子智周则撰有《成唯识论演秘》、《因明入正理论前记、后记》等。正是由于玄奘的翻译及其数传弟子的注疏,法相唯识之学才盛行于唐代。
近代玄奘学说的复兴,与唐代法相唯识学的盛行有所不同,明显地带上了时代的色彩。而近代玄奘学说复兴的主要标志是建立研究机构,培养弘传法相唯识的人才;高僧大德和居士、学者独立撰写着作和学术论文。
(1)建立研学机构,培养弘传人才
近代弘传玄奘学说的奠基人是杨仁山居士,他除了广搜亡佚法相典籍,从日本找回大量法相唯识的注疏,在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外,还曾建立只洹精舍,举办佛学研究会,培养弘传法相唯识学的人才。在只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学习的太虚、章太炎、谢无量、孙少侯、欧阳竟无、李证刚、梅光羲、蒯若木等,后来都在法相唯识学的研究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
在杨仁山的只洹精舍学习的欧阳竟无和太虚,后来分别创办了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法相唯识学的人才。
欧阳竟无偕其弟子吕澂,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基础上,于1922年成立了支那内学院,后又在支那内学院专门开设法相大学,招收学员64人,主讲《唯识抉择谈》,弘扬唯识学说。当时除正式学员以外,许多知名学者都前往听讲。如梁启超就曾前往听欧阳竟无讲唯识。其他如汤用彤、梁漱溟、黄树因等一些学者,也都是欧阳竟无的入室弟子,随他学习和研究过唯识学。其弟子中成就最大的,当推吕澂。他不仅协助欧阳竟无创建了支那内学院,并先后任教务长、院长等职。在办理法相大学期间,他阐明了法相大学的办学宗旨和目的。特别是在法相唯识学的研究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唯识学说。如对“性寂”与“性觉”的区别,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之异同,法性和法相的关系,佛性说和种姓说含义相通等等,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还对玄奘所传译的唯识学,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研究玄奘一系的译着和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太虚在1922年于武汉创立了武昌佛学院。这个佛学院以打破旧宗派的固执成见,革新中国的佛学思想,吸收新思潮、新方法,发扬中国的佛学为宗旨,但唯识学仍为该院重要的学习内容。如该院第一期专修科实际学习期限为两年,其中第二学年的两个学期,均由太虚亲自讲授《成唯识论》。该院先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不少是专精于法相唯识之学的。
太虚本人,虽然学通大小乘,其佛学思想的特点是不拘一宗一派。但在弘扬各宗学说的基础上,又特别致力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与弘传。因此,在他的佛学思想中,法相唯识思想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从1915年夏天起,即专心研习法相宗的主要经典《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尤以《唯识述记》及《法苑义林章》等用力最多。1918年在上海与章太炎、陈元白等创立觉社,在社内开讲《二十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弘扬法相唯识学。1922年在汉阳归元寺讲佛学,常为四众开示唯识观法。在他一生中,对法相唯识学所作的撰述共有40余篇。其中主要有:《深密纲要》、《辨中边论颂释》、《新的唯识论》、《唯识三十论讲录》、《讲要》、《唯识讲要》、《唯识二十颂讲要》、《大乘五蕴论讲录》、《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讲录》、《法相唯识学概论》、《百法明门论宇宙观》、《阿陀那识论》、《谈唯识》、《唯识观大纲》等。太虚针对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一文中所提出的“法相、唯识为两种学”的观点,先后撰有《佛法总抉择谈》、《竟无居士学识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等论文,认为法相、唯识是一种学,而非两种学,所谓“法相必宗唯识,唯识即摄法相”。他的这一观点,与欧阳竟无的“法相唯识非一”的观点针锋相对。后来,由太虚及其弟子唐大圆、史一如等为一方,由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吕澂等为另一方,双方对此展开长期的辩论,终于形成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两大思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太虚还认为,研习法相唯识学,可以得到以下六种利益:“破除我法之谬执”、“断尽生法之惑障”、“解脱变坏之业报”、“满足心性之意愿”、“成就永久之安乐”、“证得无碍之清净。”这些说法,充分体现了法相唯识学是太虚佛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韩清净也于1921年在北京组织法相研究会,集会员数十人,开讲《成唯识论》,传习法相唯识之学。1927年,他根据法相宗的判教,将释迦一代教法分为有教、空教、中道教的三时教,而法相宗为中道教,遂将法相研究会改名三时学会,以阐扬印度佛学和佛教真实教义为宗旨,亦即专门讲习、研究法相唯识之学,译述并刻印法相唯识典籍。韩清净任会长,全盛时期约有会员60余人。每周向会员讲演唯识学,出版亦以法相唯识为主。数十年中,培养了不少专弘法相唯识的人才。1934年上海影印的《宋藏遗珍》,其中有关法相宗典籍46种,即由三时学会印行。韩清净本人对唯识学的六经十一论都做深入研究。先后着有《唯识三十论略解》、《唯识三十颂诠句》、《唯识指掌》、《成唯识论述记〖KG*9〗讲义》、《因明入正理论科释》、《解深密分别瑜伽品略释》等。对《瑜伽师地论》和《摄大乘论》特有研究。相传他在讲演《摄大乘论》时,一字一句都能指出其来自《瑜伽师地论》的某字某句。曾对《瑜伽师地论》详加校订,撰成《瑜伽师地论科句》40万言;又融会本论前后文义,综考所有有关论着疏释,撰成《瑜伽师地论披寻记》70万言,以阐发《瑜伽师地论》奥义。其后又将两书合并,辑为《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100卷、16册。时人将他与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并称为法相唯识学两大家,有“南欧北韩”之誉。其弟子朱芾煌、周叔迦等,也都是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专家。
范古农于1948年在上海创办法相学社。他亲自撰写缘起,订立简单,编订课程,招收会员数十人。认为法相乃佛学之通途,凡学佛者皆当宗之。该社主要修学课程分为六期:第一期为《大乘五蕴论》、《广五蕴论》、《显扬圣教论?五蕴章》、《显扬圣教论?五法章》、《百法明门论》、《二十唯识论》;第二期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摄大乘论世亲释》、《辨中边论》;第三期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第四期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第五期为《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瑜伽师地论?摄释分》;第六期为《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料简》、《成唯识论述记》。范古农本人除在法相学社亲自授课外,还编辑《法相学社刊》,刊载法相讲义及重要论文。1951年范古农逝世,法相学社遂无形停顿。但该社也曾培养了一批法相唯识的人才。
以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学在近代确实呈现出复兴的迹象,同时也表明近代玄奘学说的复兴,明显地带上了时代的特征,与唐代法相唯识学的流传截然不同。
(2)独立撰写着作和学术论文
唐代弘传法相唯识学的主要标志是翻译有关法相唯识的典籍和撰作注疏。近代玄奘所传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则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佛教学者独立撰写着作和发表学术论文。
近代以来,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学习、研究法相唯识学的学者、专家,他们撰着了许多有关法相唯识学的着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近代佛教界、学术界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专家、学者多达数百人,撰着法相唯识学的着作多达数十种,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下五百余篇。十多年前,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张曼涛先生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辑录了近代以来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佛教学术论文,汇编成册。全书编为一百册,共收论文1776篇,作者823人。其中有关研究玄奘及法相唯识方面的论文有228篇,作者127人,编为14册。这在全书中比重是最大的。在这14册中,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又分为九类。其中《玄奘大师研究》二册,收文章35篇;《唯识思想论集》三册,收文章57篇;《唯识典籍研究》二册,收文章35篇:《佛教逻辑专集》二册,收文章32篇。其他尚有《唯识学概论》、《唯识问题研究》、《唯识学的论师与论典》等专集各一册,共收文章79篇。我们从这些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研究法相唯识学的盛况。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近代玄奘所传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二)复兴的主要原因
玄奘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复兴,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
(1)从日本找回久已失传的法相唯识注疏
宋元以来,由于唐武宗灭佛及五代战乱,有关法相唯识的注疏散失殆尽,以致人们无法对之进行研究。1878年,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伦敦结识了日本着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后又通过书信往来,畅谈佛学,从此得知在日本流传的中国佛教典籍甚多,其中有不少是中国早已佚失了的。1890年,其内弟苏少坡去日本,即专门托他带信给南条文雄,请其广求中国失传的古本佛经。后来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中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总数达300余种,其中有关法相唯识书的注疏多种,如《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等。这些注疏从日本找回后,杨仁山即于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从而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纷纷对之进行研究和传诵,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2)唯识思想在近代受到一些人的推崇
法相唯识的古德注疏经杨仁山刻印流通后,一些学者经过学习和研究,均推崇备至,认为它包含了全部印度大乘佛学的基本内容,学佛者首先应该学习法相唯识学。
首先对之广为宣扬和推崇的,乃是杨仁山本人。他在《与桂伯华书》中,曾特别强调要“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之楷模”。他认为只有弄通了唯识思想,才能使人“不致颟顸?NFD55?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并把它看做是“振兴佛法之要门”。因此,他在重兴法相之学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吕澂对法相唯识之学也十分推崇,称玄奘之学是“真佛学”,认为佛所说法,一切皆是法相。因此,“说法相即是贯彻佛所说法之全体”。他的结论是“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内学》第二辑)。
范古农对法相唯识学更为推崇,尝说:“佛经高深莫测,非论难得确解,而疏释论文,莫过慈恩宗。”又说:“学理高深,莫逾《成唯识论》,行持方法,莫详《瑜伽师地论》。”他还在《法相学社缘起》一文中,阐述了法相唯识学在佛学中的地位。他说:“唐代玄奘法师游学印度,归译诸论,弟子传习,为法相宗,此盖与他宗对立而言。论其实际,法相乃佛学之通途,凡学佛者皆当宗之。”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虽然对唯识思想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在实质上,它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第三卷,第228页)。但却不得不承认,“唐初势力最盛的宗派是唯识宗……就名理教养和概念体系来说,这一宗派的理论可说是达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学的顶峰”(同上,第143页)。又说“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唯识思想“也包含有一些心理分析的内容和一些合理的因素”(同上,第205页)。
其他如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等,都曾对法相唯识学进行推崇,这里不一一列举。以上这些学者的竭力推崇,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唯识学精致的名相分析对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有帮助
法相唯识学的论证方法十分精致。它运用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把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物质现象和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纳成五位百法(心法八、心所有法五十一、色法十一、心不相应行法二十四、无为法六),作了详尽的论述。它的内容包括了宇宙观和人生观,心理学和伦理学以及认识论、因果论、真理论等各个方面。尽管这些分析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十分精致。它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深化了人们的思维方法,在认识上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特别是这种名相分析方法,对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中国近代有些思想家和学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纷纷到佛学的法相唯识学中去寻求这种方法,用以整理“国故”,发扬传统思想的。如梁启超把它看做是影响文化艺术的一种动力,说成是“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谭嗣同也运用其中的思想范畴,组织了他的《仁学》,认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按即法相宗)之书”(《仁学》,《谭嗣同全集》,第293页)。章太炎自称其学术思想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即开始是由儒学转到佛学,最后又从佛学回到儒学,也是深受法相唯识学的影响。他晚年组织国学讲习会,整理传统思想,受到法相唯识学中名相分析的影响很大。梁漱溟则把法相唯识学作为观察文化和研究知识的方法。他曾公开宣称:自己“研究知识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于唯识学”。又说,他在研究知识时,“所用的名词就是唯识家研究知识所说的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9页)熊十力也是以唯识思想作为他研究学问的基础的。他最初尊崇佛学唯识论,后又渐觉其失向转向儒学,并以儒家思想改造唯识思想,撰成他的《新唯识论》。他曾说:“《新论》实从佛学演变出来,如谓吾为新的佛家,亦无所不可耳。”(《新唯识论?功能上》)后来又说:“《新论》包罗儒佛而为言,既自有根据,非同比附;而取舍贯穿又具有权衡,纯是破除门户,一以真理为归。吾中国人也,又老年人也,所见自不出中国。中国哲学思想,不外儒佛两大派,而两派又同是唯心之论,故吾会通儒佛及诸子,析其异而观其通,舍其短而融其长,于是包络众言而为《新论》。”(同上《附录》)这是说,他的《新唯识论》是以唯识思想为基础而演变出来的,最后又用儒家思想改造了佛学唯识论。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对玄奘所译《成唯识论》的唯识思想,从宇宙观到认识论都作了批判与改造,进而把中国儒家固有的思想、概念和语言,搬进了佛学唯识论,使印度大乘唯识思想,趋向中国化。这也充分体现了唯识思想在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起的作用。
正是由于唯识学中的名相分析方法对整理中国传统思想有帮助,所以一些思想家和学者都竞相研习,从而推动了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4)与唯识思想密切相关的因明为近代学者所重视
佛家的因明,是印度瑜伽行派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玄奘曾系统地介绍了因明,翻译了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并对弟子们进行了系统的讲授:其弟子辈据师口授,竞相传习,撰有注疏几十种。特别是其弟子窥基所着《因明入正理论疏》,资料丰富,解说详明。因此,因明学说曾在唐代流行一时。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很重视逻辑,加上玄奘所译因明论书,文字简拗,难以读通,终于使因明学说很快被人们所遗忘。到了近代,情况有所不同,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开始认识到应该注意逻辑。当时,有些人注意到了古代的名学,有些人则注意到了佛家因明,表现在数十年间先后出版的因明专着多达十多种。其中着名的有吕澂的《因明纲要》、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陈望道的《因明学》、太虚的《因明概论》、虞愚的《因明学》、周叔迦的《因明新例》、覃达方的《哲学新因明论》、熊绍坤的《因明之研究》等。有关因明的学术论文就更多,张曼涛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就收有32篇。此外,当时的一些佛学院校,大都开设因明课程。不仅如此,一些有名的文科大家,也有讲授因明的。如太虚、覃达方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授过因明课。熊十力、熊绍坤、周叔迦等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讲过因明。周叔迦一度还曾在民国大学讲授过《因明入正理论》。史一如曾在中国大学开讲“佛教伦理学”。此外,王森在清华大学和中国大学,陈望道在复旦大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都开讲过因明。即使是远在云南大理的中国民族文化学院,也开设有因明课程。
以上这些情况,一方面表明了近代学者对因明的研究有所成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因明与唯识思想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凡是研究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学的,大都重视因明的研究。正是由于因明之学的流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综上所述,玄奘所传法相唯识学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复兴,并由此而推动了整个佛学的复兴,除了杨仁山从日本找回法相唯识的古德注疏,并刻印流通外,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法相唯识思想的本身包含有许多积极因素。因此,在近代中国,所有学佛者,包括所有佛教院校的学僧,佛教新兴团体的一些居士,几乎无一不以法相唯识之学为必修的一课。而各宗各派的佛教学者,凡是研究佛教理论的,也大都注重法相唯识学,所谓“教宗法相,行在弥陀”。如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原是专弘净土的居士团体,但从1926年起,即组织研究唯识学会,请太虚为导师,王少湖、李荣祥等为指导员,每逢星期日,由太虚向会员作唯识学讲演。平时则由指导员指定有关唯识论书,自行学习。1928年组织的佛学研究会、暑期讲学会和1931年开设的星期佛学研究会等,也都由太虚、范古农等担任指导员,学习各种唯识论书。其他一些佛教团体,开讲唯识学的也很多。
不仅如此,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也竞相研习法相唯识学。他们不仅把法相唯识学作为自己建立理论体系的依据,而且还在一些高等学校里讲授唯识课程。如邓伯诚、张克诚、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均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讲唯识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讲《百法明门论》;唐大圆、张化声在武汉大学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刚于东北大学讲《成唯识论》;梁启超、王恩洋则分别于清华大学和成都大学讲唯识学。从此,唯识学逐渐进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玄奘所传法相唯识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