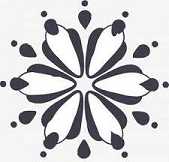吕澂与熊十力论学函稿评议
发布时间:2022-07-13 10:09:51作者:楞伽经讲什么一、从蓝吉富先生的悼念吕澂之死谈起
近四十年来,大陆的吕澂先生和在台湾的印顺法师,一直被视为在佛学研究上的「双璧」,是成就非凡的两个高峰。但文革後的吕澂先生,相当沈默,可说全然脱离了佛教学术圈而隐居起来。印顺法师在台湾的近二十多年来,虽然也大半过著隐居著述的生活,可是学术的研究环境,较吕澂先生为佳,和社会的沟通讯息也较频繁,所以印顺法师的距著出,也立刻在台湾、乃至海外华人的佛教圈流传开来。相较之下,吕澂先生的晚年,可谓寂寞至极!因此,蓝吉富先生在接到北京杨曾文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佛学研究室主任)於七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的来信,说吕澂先生已於七月八日逝世,享寿九十三(1896~1989A.D.),立即撰文评述他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载《福报》周刊,八号,七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蓝先生除了扼要地全面介绍吕澂先生的生平,著述和学术成就之外,还特别就吕澂的「风格与际遇」和日本前辈学者宇井伯寿作一比较,指出两人才学相当,而一落寞(吕),一风光(宇井)且学风的影响,有天渊之别。蓝先生因此深有所感地说:
「整个现代中国的大环境,似乎并不需要吕澂这样杰出的学者。......最令人感到怅然的,不只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也不祗是其学术思想的後继无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扫除他所认为的佛学上的『重重障蔽』与『错误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齐放,盛行一时。」
蓝先生文中提到吕澂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和《梵网经》的批判之外,还提到他(吕澂):「看不起熊十力的思想及熊氏的《新唯识论》,认为熊氏思想如『浮光掠影,全按不得实在』,然而熊氏思想却甚受海外华人哲学界重视与欢迎。」面对这样的学术环境,蓝先生为之怅然地:
这些现象不祗烘托出哲人的孤独,也显示出治学的艰难。而且也不禁使人怀疑,宗教与学术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宗教是否有必然的关涉?」
读到这段沈痛的文字时,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读完後,马上挂长途电话,与蓝先生谈了良久;但也只能感慨而已!
我个人在佛学研究上,比较注意中国近世佛教思想,因此对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大陆佛教和光复後的台湾佛教现况,皆长期留意。吕澂先生和印顺法师的著作,不用说,都曾仔细地翻读过了。有关印顺法师的思想,我已撰文讨论过一些;至於吕澂先生的著作,则未正式讨论。如今,吕澂先生已过世,我想就蓝先生前面提他批评熊十力思想的部份,加以讨论。由於此事关涉中国近代儒佛思想的趋向,至为重大,假如可能的话,是需要专书研究才能交代清楚,我目前忙於其他论文研究,无法对此细论,只能扼要的提及罢了。希望国内的通家,不吝指教才好!
二、研究史概述
有关〈吕澂和熊十力论学函稿〉,在台湾目前可见到此一完整资料的地方是:(一)蓝吉富先生主编的《世界佛学名著译丛》NO.48,《中国佛教泛论》的「附录一」(注1)。(二)洪启嵩、黄启霖主编的《当代中国佛教大师之集》NO.8,《吕澂文集》(注2)。蓝先生用的题目是〈吕澂熊十力论学书信集〉;文殊版的《吕澂文集》,则标明为〈吕澂和熊十力论学函稿〉。因文殊版的资料,一般读者容易取得,故我用文殊版的这标题,便於读者对照察看。其实这份资料,原载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第十一辑(注3),作者:吕澂、熊十力,题为〈辨佛学根本问题〉。台湾的资料,即由此转载的。不过,台湾出版的熊十力著《新唯识论》语体文版(注4),在卷下之二的〈附录〉中,已摘述过。只是熊氏并未指明对象是吕 ,且非全引,故一般读者无从知道:向熊十力提出问难的人是谁?熊十力的高徒牟宗三先生,在其佛学著作《佛性与般若〉上册的〈序〉(注5)中,也提到吕澂写信给熊十力说:「天台、华严、禅宗是俗学。」牟先生不同意吕澂的「力复印度原有之旧」,责吕澂先生的观点为「浅心狭志之过也」!另外,研究新儒家的蔡仁厚先生,在其所撰的《熊十力先生学行年表》(注6),也载吕澂与熊十力书信论辩之事。但只提熊十力与吕澂商量欧阳竟无死後,「支那内学院」如何处理的事。丝毫未引吕澂批评熊十力的部份。牟、蔡二人,皆是亲熊十力者。吕澂在信中严词批评熊十力,以及熊露出无招架之力的「窘态」(详後),皆非可夸耀於人的光彩事。未多加交代,实人之常情也,不必深责。但是,自《中国哲学》披露〈辨佛学根本问题〉後,就双方书信内容,加以讨论的,据我所见,有二个人:(一)是大陆专研熊十力思想的郭齐勇先生,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态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五十年来佛教界的批评」(注7),曾概略提及吕澂先生的观点,同时也指出熊十力以「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来应付(注8)。(二)是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先生,他在《新儒家哲学について─熊十力の哲学》(注9),第六章「熊十力の《新唯识论》」,也提到《中国哲学》上的论辩书信,以证明「支那内学院」对熊的反感。结合上述资料来看,学者们提到吕、熊论学书信,仍属稀少,且往往语焉不详,难窥全貌。因此,在本文中,我想将双方的争辩背景、争辩内容和时代的意义二者,分别以思想史的角度,来作一回顾和检讨。
三、争辩背景的考察
争辩的导火线
从双方的书信来看,发生争辩的直接因素,是欧阳竟无(1871~1944A.D.)於一九四三年二月,病逝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吕澂将讣闻函告熊十力,要熊撰文悼念;熊以「传师之日浅,又思想不能为佛家」(注10),委婉拒绝,同时又附有一封熊寄梁漱溟的论欧阳信稿,批评欧阳之学,是「法相唯识」,虽愿力大,惜其「原本有宗,从闻熏入手」。熊不客气的说,欧阳一生鄙宋明德,其实宋明儒的「鞭辟近里切著已」,无资外铄,正是欧阳所短,而要学习的。熊还本此立场,指出欧阳谈禅,「不必真得力於禅」;欧阳学解以「闻熏」入手,故内里有「我执」与「近名」等许多「夹染」;胸怀不够「廓然空旷」,有「霸气」,为文「总有故作姿势痕迹,不是自然浪漫之致也」。熊最後称自己的《新唯识论》,融通儒佛,自成体系,是「东方哲学思想之结晶」,和欧阳的学问宗旨相比,就像陈白沙(1428~1500A.D.)之於吴康斋(注11)。亦即熊认为自己是「青出於蓝,更胜於蓝」了。按:熊曾随欧阳读唯识(详後),平生得力的佛学,实奠基於「支那内学院」就学时期。熊也坦承:「吾师(指欧阳)若未讲明旧学(指护法系的唯识学),吾亦不得了解印度佛教,此所以不敢忘吾师者也。」(注12)既然师恩如此之大,纵然日後为学的取径有异,也不必於恩师新逝之际,这般露骨地的批评。若照传统的中国社会伦常来看,熊之此举,可谓不近人情。信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寄出的,熊不久就发觉信中言语及附信,甚不妥当,在吕澂先生未回信前,又於同年三月十六日,再寄一信,说自己「施知僭妄,幸勿示人」(注13)。但已太晚了!吕澂先生於同年四月二日,回信熊氏,针对「闻薰」一词,提出强烈地质疑(注14)。於是双方正式展开对佛学精义的热烈争辩。
熊对欧阳积存已久的不满因素
熊十力生平脾气暴躁,好骂人,是稍识熊者皆知之事(注15)。但熊对欧阳的批评,岂祗月旦彼此宗旨不同而已,真可谓「不满」、「讥讽」和「怨怼」之情,跃然纸上!何以熊的当时心态是如此强烈?师徒之间是否有过不快?主因是熊著《新唯识论》和师门立异而起的。自一九三二年《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刊行以来,不久即有「支那内学院」的刘定权撰《破新唯识论》,由欧阳作〈序〉,发表於《内学》第六辑。欧阳在〈序〉中痛责说:「六十年来阅人多矣,愈聪明者愈逞才智,愈弃道远,过犹不及,贤者昧之。而过之至於减弃圣言量者,惟子真为尤,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省以相从」(注16)。可见其对熊十力立异说的不满!刘的这篇文章,过去不易寻觅,故见者少。反而熊十力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破〈破新唯识论〉》,因附於《当代儒佛之争》在台湾出版(注17),故知者较多。现因新编的《熊十力论著集》第一册出版(注18),收有〈破新唯识论〉全文,我们已能据此比对双方论点,才知刘氏论证法度谨严,见解精邃,甚能摧破熊氏要害。其中对唯识学和般若学的文献分析,扼要、明确、熟练,引用中国传统经论来酬对和反驳,亦顺适中节。後来批驳熊的文章,除印顺法师的〈评熊十力《新唯识论》〉(注19),以西藏正统中观空义驳熊之外,罕有超过者。在此,限於篇幅,无法详述双方初次交手的内容。但自後,熊十力和「支那内学院」决裂,欧阳门下的王恩洋和陈真如等都曾撰文批评熊十力。欧阳本人於一九三九年七月,在〈答陈真如论学书〉一文批评熊不懂佛法的宗趣──「无余涅盘」,又错解儒家义理,「杂糅孔佛」。同年十二月在〈与熊子真书〉,除了要熊「多闻圣言,念念思惟」,以生悲智,正解佛、孔之言外,并要熊将斯旨达诸(梁)漱溟(注20)。可以说,熊与欧阳之间,始终存有隔阂的相异观点,加上熊的脾气暴烈,率性任情,自尊心又特强,久历的不满,在论及欧阳时,自会从内潜而外铄。只是在欧阳新丧之余,时机不太对罢了。
吕澂维护师门的心理因素
吕澂对熊十力的反驳,也不纯然是思想不同,而是有心理因素的。吕投师欧阳於一九一四年。当时吕澂是十八岁,欧阳是四十三岁。由於追随早,故师徒情份深厚。据许逖先生在〈吕秋逸先生轶事〉一文(注21),引述其师方东美先生的话,吕澂初投师时,曾献一纸条称:自愿终身不离师门。抗日战争爆发,「支那内学院」迁蜀避乱,流寓江津,吕澂随侍师侧,照顾欧阳的生活起居。欧阳生性刚烈脾气甚大。有一次发火,连吕澂都无法承受,而谢师求去。但吕澂走後,欧阳日常生活顿乏人照顾,相当艰辛。不久,欧阳病重,思及吕澂尚存授师纸条,令人通知吕澂亲自取回。吕澂得信後,即刻赶回江津,投地跪於欧阳足下,师徒相对痛泣,从此未再离师门一步!溯自追随的初期,迄一九四四年,欧阳逝世为止,师徒共处三十余年之久。欧阳死後,吕澂先生还将「支那内学院」,维持至一九五二年,才在中共的政治压力下宣告结束。此种毕生奉献师门的高谊,正如欧阳当年与其师杨仁山先生(1837~1911A.D.)的相知和受事业的嘱托。吕澂後来在给熊十力的信上(注22)说:「论齿,兄则十年以长;论学,弟实涉历较多。弟值竟师,既已寝馈台,贤五载[弟於宣二(1910A.D.)读内典,民三(1914A.D.)遇吾师]。及知左右,又已尚友唐人十年。」换句话说,吕澂虽较熊十力年轻十一岁,但学佛的经验较熊更丰富。在熊到「支那内学院」(1920A.D.)之前,吕澂参与欧阳经营「金陵刻经处」和校刻《瑜伽师地论》多年,欧阳在一九二四年以後的思想成长,乃至研究法相唯识学有成(详後),吕澂知之最深。而吕澂通日、英、法、梵、藏各种语文,得以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了解世界佛学研究动态,突破向来依靠传统中文译本藏经的限制。因此,熊遇吕之时,吕已是知名的师资辈大家了(注23)。原先蔡元培(1867~1940A.D.)要聘吕澂先生赴北大讲唯识(时在1922A.D.),欧阳不放,遂改由熊十力北上(注24)。如非这机缘,熊十力能否在北大成名,实难以逆料。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体会到吕澂日後不满熊十力的出言不逊,是含有相当复杂的心理因素在内。
双方思想葛藤的渊源
熊十力出身欧阳门下,日後与师门决裂,绝非一桩寻常的士林葛藤而已。它代表了近代中国佛学的复兴和儒佛长期冲突的再次爆发,实在是民国以来传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交代。唐代正统唯识学在民初的复兴,是文化界的大事。但欧阳的关键性角色,又是如何出现?如何扮演呢?欧阳的复兴唯识学,是因校刻《瑜伽师地论》所引起的。清末,杨仁山在南京城北延龄巷创办「金陵刻经处」,透过南条文雄的协助,由日本取回散逸的佛教古藉多种,刻板流通。经论中,最重要的,是唐代窥基(632~682A.D.)著的《成唯识论述记》和玄奘(600~664AD)译的全本《瑜伽师地论》两种。杨生前已出版《成唯识论述记》(1901A.D.)。杨并曾办佛学研习部,欧阳、太虚(1889~1947A.D.)、谭嗣同(1866~1896A.D.)等皆曾受教门下。辛亥革命前夕(1911A.D.),杨仁山病故,临终前,将「金陵刻经处」的事业,嘱咐欧阳。按徐平轩撰〈文革前一篇关於整理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工作报告─整理金陵刻经处的经过与完成〉(注25)一文,说杨将「金陵刻经处」咐嘱弟子三人:陈□庵、欧阳、陈宜甫分任流通、编校、交际三职。一直到一九一九年,欧阳因另创「支那内学院」迁出「刻经处」为止,都是业务最盛的时期。但杨嘱托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欧阳将其生前校勘已半的《瑜伽师地论》完成、出版。这对欧阳是个难题!在此之前,欧阳虽经历:汉学→陆、王心学→《起信》和《楞严》等传统佛学的变迁(注26),但对唯识论学并无深研。而清末治唯识论,特别是治《瑜伽师地论》有成绩的,是革命家、国学大师的章太炎(1868~1936A.D.)。章因「苏报案」系上海狱中,开始精治《瑜伽学》,其後并依《论》中「三性无性义」,撰〈建立宗教论〉及〈齐物论释〉等著名文字,对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冲击甚大。章的佛学知识,虽部份得自日人如常盘大定等的著作,但主要是以「考据学」的治学方式,自己摸索出来的。其佛学论文,非为学术目的,而是用来驳基督教的神教思想,对抗西洋文化的优势入侵,并从事鼓吹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这一强烈批判性的文化民族主义作风,不但是谭嗣同《仁学》革命思想的深层化,并为此後的思想界开启藉佛教唯识论批判文化思想的强大取向。欧阳竟无却因个人遭遇而形成的特殊隐退心态(注27),采取了不同於章太炎的佛学进路。他说:「渐之学佛与他人异。我母艰苦,世叔所知。病魔生死,儒既无术应我推求,归根结蒂之终,下手之门之始,亦五里堕雾,彷佛依稀。乃於我母谢去之一时,功名富贵、饮食男女,一刀割断。厕足桑门,四方求师友闻道,转展难偿,甚矣其苦也!三十年读书,求诸西方古人,乃沛然有以启我。家不幸,女兰十七从予学於金陵,予以刻经事入陇,归则殃殁。中夜恸哭,既已无可奈何;发愤读书,常达旦。於时《瑜伽》明,《唯识论》豁然!」
可以说,他的学佛历程,和家人丧亡,骨肉情深,大有关系。以如是之心态治佛学,宜其契入深、信学坚,全生命投入求寄托之故也。问题是:欧阳的收获是甚麽?意义何在?章太炎的唯识学仍无佛教发展史的概念,他的诠释法多为横的推衍,较忽视纵的长期演进之探索。欧阳则以「弥勒学」展开的立场,区分「法相」与「唯识」。因欧阳在校勘时,同时比对其他相关典藉,於是提出应将「法相」与「唯识」分宗的意见,他以「十要」来说明其纲领,以「十支」来说明其思想,并以「十系」:一、弥勒,二、无著、三、世亲,四、陈那,五、护法,六、戒贤,七、玄奘,八、窥基,九、慧沼,十、遁伦,来说明从印度到中国法相与唯识学的流传状况。有体系地将「瑜伽系」的思想,完整地叙述到了。这在唐以後的中国佛学研究史上,是没前例的。故一九一八年《瑜伽师地论》出版,并附有欧阳所撰的〈长叙〉,「使慈宗正义,日丽中天」,号称唐代玄奘以来的最大成就(注28)!章太炎对欧阳的区分「法相」与「唯识」,盛赞其说,称之为「独步千祀」(注29)!此一成就,确立了日後「支那内学院」师生以法相唯识学为核心的佛学思想取向。吕澂对藏文《摄大乘论》的重译及在《瑜伽师地论》中发现《杂阿含经》的「本母」资料,也是沿续此一学风而来。严格而言,以学术论学术,《杂阿含经本母》的发现和经文秩序的刊定,是世界性的成就,不但玄奘本人未曾梦见,连日本学者姊崎正治竭数年之力,对勘巴利文及汉译藏经的结果,也不及吕澂的发现。但是,当时对社会而言,强调的是欧阳的复兴正统的唯识学,亦即专业性的唯识学专家,取代了「章太炎式」的佛学言论主导权。「支那内学院」的创立,就是透过教育和研究,对此学说的强化,自此之後,也一直是此学派的重镇。对於想接触法相唯识学的学者,毫无疑问地,会被吸引而来,梁漱溟、熊十力、乃至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也到欧阳处执门生礼,就没甚麽好大惊小怪了。
熊十力是因梁漱溟的介绍,於一九二0年,到南京追随欧阳竟无。在此之前,他是深受王船山(1619~1692A.D.)影响的自学者;同时在中年以前,也有清末从军、民初革命的军事挫败经验。这些因素,使他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倾向於为学济世的襟怀。他於前往南京拜师之前的思想,都呈现在一九一八年自费出版的小册子里,书名叫《心书》,是一些读书笔札的汇录。他说这是「生卅年心行所存,故曰《心书》。船山有言:唯此心常在土壤间,或有谅者」(注30)。蔡元培为他写的〈序〉里提到:「......今观熊十力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净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注31)事实上他在书中流露的,是一种读书人对时局忧患的关怀与批判意识,称不上博学,也未见深入的佛学理解。如〈船山学自记〉,只有一段提到:
「余曩治船山学,颇好之,近读余杭章先生〈建立宗教论〉,开三性三无性义,益进讨竺坟,始知船山甚浅。」(注32)
於〈示韩浚〉中,将《中庸》的「无声无臭」和斯比诺莎的「泛神论」相比,而称「佛明因缘」为「戏论」,且佛说「唯心,与此云无神,精粗迥别也」(注33)。在〈张纯一存稿序〉中则赞同:将「儒教的礼」和「净严心土」相比;《新约》之「上帝即一真注界,祈祷具戒定义」。可以说,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复张君〉一文,大半引章太炎的〈大乘佛教缘起考〉。但对章太炎要「振起姚江学派,以挽今世颓靡巽懦之习」(注36),他相当不以为然,认为阳明学风是造成晚明「气矜亡国」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他日後对「阳明学」的吸收和推崇是相当热切的。这当中的转变关键,几未见研究熊十力学说者提及。我认为是来自梁漱溟的影响。熊十力在思想上的转变过程,宛若梁漱溟的翻版,可以说是「唯妙唯肖」地在学习梁漱溟的为学途径。熊在一九一三年曾於梁启超(1873~1929A.D.)所办的《庸言》上发表笔记,赞扬《淮南子》的思想,而指斥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注37)。梁漱溟则於一九一六年在《东方杂志》(注38)发表《究元决疑论》,引用法人鲁滂的「以太涡动说」,比附佛教之如来藏或阿赖耶识,所谓融相入性,发挥《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的染净同体思想,以诠释世界所以形成之理。又於文中指责熊十力对佛教的批评是出於无知。熊十力居然虚心接纳,并於一九一九年致书当时在北大任讲师(案:讲授《印度哲学概论》)的梁漱溟,希望有机会晤谈。同年熊十力特由任教的天津南开中学,赴北京借住广济寺,约见梁漱溟共谈佛学。从此二人交往近四十年之久。
熊十力在《真心书》中仍保留一篇〈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注39),全是摘录梁的话,可见熊对此种思想的喜爱。一九二0年暑假,梁漱溟因黄树因的介绍(黄树因南京人,与吕澂同事欧阳竟无,通梵、藏文。曾在北京随俄人刚和泰学梵文,并在北京雍和宫抄录西藏文佛典。惜早死,吕澂向在语文方面受其影响甚大),访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支那内学院」正筹设中),向欧阳请教唯识学,至为钦佩(注40),除极力宣扬之外,并介绍熊十力前往求学。熊在「支那内学院」前後(1920~1922冬)二年余,攻读甚力。
梁漱溟是北京顺天中学毕业,也曾参与清末革命,民国後对革命失望,放弃升学,开始寻求佛法,在家自习。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岁,因发表《究元决疑论》,获蔡元培赏识,聘为「印度哲学概论」讲师。一九一七年开始任教,先讲印度哲学,後增授唯识述义。一九一八年,其父梁巨川投水殉清,促使他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一九二0~二一年,开始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宣称使用唯识学的概念,可诠释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以「意欲向前」代表「西洋文化」的特色,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以「意欲反身要求」为「印度文化」的特色(注41)。在书中,梁还指出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印度、西洋皆不同(注42);又说今後文化的发展,应取法孔子不求计较、刚健和谐的生活态度;并效法泰州学派─阳明弟子中最富平民作风的一派。──再开创讲学之风!梁漱溟的此书出版,立刻轰动各界,成为「五四运动」时,宣扬孔子学说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但梁监於自己对唯识学并无十足把握,决定另请欧阳门下的专家,前来代讲。徵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後,於一九二二年,赴南京「支那内学院」,原欲聘吕澂北上,但欧阳以吕为得力助手,不放人,遂改邀熊十力至北大讲课(注43)。蔡元培原与熊为旧识,又得林宰平揄扬,於是同意熊担任特约讲师。可是熊讲正统唯识学一年不到,即改讲自创的《新唯识论》。这一转变,其实只是由「阿赖耶识」的「妄心系统」,转为「真心系统」,并因而倾向陆、王的心学:恰恰是梁漱溟正极力提倡的思想。
梁漱溟以唯识学的概念和方法,解析东西文化的成功,其实是章太炎模式(如〈建立宗教论〉)的新尝试。但梁漱溟宣称时局艰难,民生凋蔽,不应再过佛家的生活,使佛教的立场,面临社会的质疑。这对熊氏而言,不能没有强烈的暗示作用。因此,在梁漱溟的思想转变之後,熊也随之转变,绝不可看成巧合,而是亦步亦趋的追随!日後熊的大弟子牟宗三先生说:「他(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宋明儒与明亡而俱亡,已元百年於兹。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动了。」(注44)但,这其实是很吊诡的思想转折,而非单纯的儒学复兴问题。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曾大肆批判宋明理学,认为不如佛理之澈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则应用了唯识学的诠释法,成功地凸显孔子的生活态度。何以会如此?梁漱溟虽在北大讲授《唯识学述义》可是他诠释文化的工具,却是改良的唯识学。他仅用「意欲」、「现量」(感觉)、「比量」(理智)和「非量」(直觉)等几个概念名词罢了。并非整个唯识学复杂名相和理论的套用,不但说明上便利、清楚,也避免了原唯识学观念所可能带来的意思混淆。这是他成功之处!他更因而一跃成为和梁启超齐名的大思想家。
由於正值欧战之後,西洋科学文明破产、东方文明复兴的呼声,正普遍流行,梁漱溟正好成了这一「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成就还促成了唯识学的学习新热潮;而他在书〈序〉中宣称要学正唯识,须赴南京请教欧阳竟无、吕澂和梅光义(注45),顿使欧阳、吕澂等受到各方的瞩目。但是,梁漱溟的诠释理念,其实是融入了柏格森和罗素的最新学说:前者重直觉,讲生命流行;後者强调创造冲动说,使生命具有积极的功能。因此梁的「意欲」观念,已被冲淡了「虚妄」的色彩;而重直觉,恰与阳明学应合。於是「妄心系统」的唯识学,无形中又转回《大乘起信论》的「真心系统」了。梁漱溟因此後非以一专业佛教学者讲唯识,欧阳的学术取径尽管未必符合本身信念,却不妨给予相对的尊重而免於冲突。熊十力则在北大靠讲「唯识学概论」为生,必须运用唯识学名相来诠释自己的「体用不二之玄学」,因此在概念上的冲突和混淆,一时也无法解决。等到他於一九三二年,将《新唯识》出版时,他同时也是走上和「支那内学院」决裂的不归路!然而,此时唯识学的文化批判功能,早已被唯物论的共产哲学所取代,失去了影响社会的功能。新、旧唯识论之争,只成了少数专业学者的关怀点,对广大的群众而言,也成为无关紧要的学术风波了。这就是吕、熊论学时的状况。
四、争辩的内容
吕澂对熊致梁信稿的质疑(第一封信)
我们已在前面叙及两者的思想背景,在争辩的导火线中,也引述了熊十力致梁漱溟信稿,讥欧阳从有宗闻熏入手之失。对熊的这一说法,吕澂於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复信说:「来教不满意闻熏,未详何指。《瑜伽(师地)论》说净种习成,不过增上,大有异有外铄。至於归趣,以般若为实相,本非外求,但唐贤传习晦其真意耳。尊论完全从「性觉」(「与(性寂)相反)立说,与中土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安得据以衡量佛法?若求一真是真非,窃谓尚应商量也。」(注46)吕澂认为在「瑜伽系」的「闻熏」作用,本来就是净化潜能(净种)的增强,并非自外而生。而此一净化潜能的增强,其最终目的,是亲证智慧解脱的境界,也不是外求。至於「唐贤传习晦其真意」一语,是指安慧对《唯识三十颂》的诠释久被淹没,只存於梵、藏本,而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只是护法一系的杂揉,非安慧本意。吕澂除重译《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外,并有<引言>说明与唐代译本的优劣之处(注47)。但,吕澂最重要的质疑点,是指出「性寂」和「性觉」的差异。是吕澂认为中、印佛法的分歧,也是吕澂毕生治佛学的关怀点所在。吕澂後来所写的论文,如:
1.<禅学考原>(注48)2.<谈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注49)3.<探讨中国佛学有关心性问题的书札>(注50)4.<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注51)5.<《起信》与禅--对於《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注52)6.<楞严百伪>(注53)都是探讨「性觉」思想,如何和禅学合流的问题。其中四、五两篇,关於《起信》和《楞严》的伪作揭发,更是用尽苦心。虽然欧阳及其门下王恩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即於「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料拣《大乘起信论》,并批评天台、华严的佛教思想,对「真如」能否「受熏」提出质疑。
但当时吕澂似乎将注意力放在文献学的校勘上,未专於心性论的问题作文章。亦即如藏文中安慧的注释和《摄大乘论》等的整理,是对唐代唯识学疏注的再检讨,比批评中的传统宗派思想的得失,要为更根本地作厘清。可以说,他一方面维持「支那内学院」的唯识传统立场,一方面又在文献证据下功夫,使思想的争论更是学术性格。故当熊十力提出「闻熏」问题时,他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反驳!虽然此五篇文章,都写於和熊书信争辩之後,但在争辩时,吕澂的关涉已相当清楚了。他指出熊的思想为「性觉」,是《起信》、《楞严》一路的,即为前此的研究和此後的探讨取向,作了有力的说明。
熊十力的初次答辩(熊的第三封信)
熊十力在同年四月七日,回信说:「尊论欲融法相以入『般若』,谓不外求。然力之意,则谓必须识得实相,然後一切净习皆依自性发生,始非铄。」(注54)然後,熊氏依自己的观点,批评吕澂说:「今入手不见般若实相,而云净种习成,以为增上,此净种明是後起,非自实相生,焉得曰非外铄耶?」(注55)在熊氏的思相逻辑里,「净种」多与「实相」相干,必须是前者由後者所生,否则「净种」增上後,才归「实相」,那麽此一「般若实相」,即是有欠缺的,只能「偶然」地获得而已。顺此推论再发展下去,则「空宗」和「有宗」的融通,即无必然性的关系。(注56)在前一封信,吕澂原意是要证明「净种习成」非外铄,而「归趣,以般若为实相」,亦非外求,故「闻熏」当然是内在潜能(净种)的增强而已!熊氏既认吕澂的「净种」和「实相」,并无「相生」的关系,则「空、有」二宗之分,势所必然(因难以融通)。这是第一点的答辩。但吕澂在前一封信中,已点出熊氏的思想理路:是「性觉」;而非「性寂」,与中国历来流传的「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注57)(页二六O),熊氏自当答辩。按:民国以来,中国佛学界受日本学界研究风气的影响,针对《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传译有争论典籍,掀起了「批判伪经、伪论」的风潮(注58),熊十力自然知道吕澂说的「伪经、伪论」,所指为何?不过文献学的考据,非其所长,所以他说:「此等考据问题,力且不欲深论。」(注59)然而,在熊氏的意见中,纵然「伪经如《楞严》、《圆觉》等等,是否中土所伪,犹难遽断;伪论如《起信》,其中义理,是否无本於梵方(案:即印度佛教)大乘,尤复难言」(注60);但吕澂所主张的「性觉与性寂相反」,他是不能「苟同」的。换句话说,熊十力依然坚持「性觉、性寂不可分」。他的理由如下:
「般若实相,岂是寂而不觉者耶?如只是寂,不可言觉,则实相亦数论之也。佛家原期断尽无明,今冥然不觉之寂,非无明耶?而谓自性如是,毋乃违自宗乎(注61)?」「言性觉,而寂在其中矣。言性寂,而觉在其中矣。性体原是真寂真觉,易言之,即觉即寂,即寂即觉(注62)。」
「从宇宙论的观点而谈法性,只见为空寂(空非空无之空),而不知空寂即是生化者,是证到一分(空寂),未识性体之全也(注63)。」「觉者,仁也。仁生化也。滞寂而不仁,断性种矣。」(注64)
按:吕澂在前信中,只言「性寂」与「性觉」相反,并未对两者下定义;充其量,只能就他指摘「性觉」与「中土一切伪经、伪论同一鼻孔出气」的文意,看出熊氏的「性觉」论,近似《楞严》、《起信》的立场,或暗示有源自「伪经、伪论」的可能罢了。熊十力则据本身思想立场,加以引伸的诠释,不但强调「寂」、觉」一体,更指「觉」为「仁」、为「生化」。如此一来,他即可声言:《新唯识论》语体本(中篇),备发此意,「贵乎观儒佛之道也」(注65)除此之外,熊氏认为上述道理,他「确是反己用过苦功,非敢与诸佛立异」。既然他有这一经验为依据,外在的文献考证,便非属必要。因而,他劝告吕澂说:「治经论是一事,实究此理,却须反在自身找下落。......其或有未会,不可遽非前哲,亦不可遽舍亡,以徇经论。廓然忘怀,默而已。久之会有真见处也(注66)。但,就论辩的角度来说,熊诠释的最後依据,既然是取决於他个人「内证」的经验事实上,已无正、误或真、伪可言。因不管对手辩论术如何高明,或如何渊博且精确地引据资料,都不可能说服熊氏。理由是,熊氏只要声言:他的经验显示为何,便可拒绝对手主张证据说明。文艺欣赏,有一著名的格言:「谈到趣味无争辩」,很近似这种取证「内在」的情形;我们对这种「主观」的诠释,或许不能忽略其思想的韵味或价值,但可预测:如辩论,则将是「各说各话」的下场。
既然如此,为使论辩内容,有一衡量的基准,我们势须再重新检讨熊「经验内容」并举例证来说明。
在检讨重点上,我们要追踪熊本人自承的「经验内容」是什麽?是否有较具体而足以说明的言论?假如有,熊即必须面对学术逻辑的分析,而不能任意游移语意。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常运用技巧,先让对方同意某种前题,然後以此把柄,逼对方就范,接受後续的结论。由於在叙述前题时,对方已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何?故当苏格拉底提出下一阶段的後续结论时,叙述者除了俯首就范外,别无其他躲闪之法。我们探索熊氏的「经验内容」,亦可如法泡制。否则,论学云云,只成空话罢了。
要直接切入熊氏的「经验内容」,最关键之处,是他经由何种方式,将《新唯识论》的「理论」提出来。换句话说,他如何「默识冥会」?是靠禅定?或思维?然後又如何转旧唯识为《新唯识论》?我们在前面争辩背景的考察时,曾提到他遭遇概念的混淆和冲突,却未详加说明,读来可能如一头雾水,不知何指?如今,我们不能再规避此问题了。同时,汤用彤先生在一九三O年於中央大学演讲,提到的:「熊十力先生昔著《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四稿,易为同源」这段话(注67),才能有较清楚的了解。
在《十力语要》卷四(注68),有其学生高赞非,在日记中,记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间,熊授课的语言。由熊氏本人於一九四六年撰序,列为《语要》的第四卷出版。此日记,熊曾稍改字句(注69),是熊氏认可的内容。我们即据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来分析其思维方式和转变的内容。此段内容,是关於佛教「轮回问题」,熊坦言:「此事在吾心理上经过,极曲折、极繁复。」(注70)虽然熊在序中言,他一九四六年左右(与吕澂辩论後一年余),已不多谈此问题。但他的早期的思路转变,却与此大有关系。「高赞非记语」:
「先生自言,始为轮回者之信徒。其初作唯识书,虽於护法诸师之理论多所破斥,对於佛家根本观念,即轮回观念,固与护法同其宗主,而莫之相悖也」(注71)。
但是,熊氏对此「古今之一大谜」产生了抉择的疑惑。:「诸有生物,其生也,原各各独化,都无终始,不以俱尽乎?(注72)」
「抑宇宙有大生焉,肇基大化,品物流行,故生物禀此成形,其形尽而生即尽乎?」(注73)「由前之说,则生界为交遍。」(注74)「由後之说,则生界为同源。」(注75)按:这两种看法,前者为佛家缘起说;後者,则是世间一般学说常有的万物同源论。但熊氏的理解,并不正确。或则说,他问的,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说:「由前之说,则有生,皆无待而自足。由後之说,则有生将外藉而凭虚」(注76)。然後他自注说:「如吾之生,若非自有,而藉外界独存之大生偶尔分贼者,则吾生直等於石火之瞥已耳。谓吾生非自有而索源於外,外源之有,吾又何从徵之哉!(注77)」
他为了这个问题,「尝徘徊两说之间,累然而不释也」。他其实是为後者的同源问题而烦恼。因既然生命有同一来源,我即为所生,我是偶然生者;生我者根源何在?我又如何求证呢?──这是他话中的疑义,显然是把生者和被生者,视为偶然藉「生」才联系的关系,因此对生命偶然性和根源无法融为一体感困惑。如按佛教缘生的道理来看,偶然性和交遍的法则:缘合迁变,才是同一立场的;熊氏却将其纳入「有生皆无待而自足」的同源论立场,当然形成理论上的矛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体用不二」之学,最初是陷於分裂的局面!他第一次解决是:选择了「轮回说」。其自辩理由如下:「转复宁息以推求,旷然自喻,吾生之富有,奚由外铄。(注78)息骑驴觅驴之妄。(注79)悟悬的投失之非。(注80)遂乃印持前说,略无犹疑。」(注81)----这样的诠释,尽管有後期看法纳入前期的嫌疑(注82),但其倾向於万物同源论的立场,是很明显的。故他虽信「轮回说」,於理可成立,终不能久安也。高赞非说,熊氏「一日忽毁其稿。怅然曰:吾书又须改作矣。」(注83)原来熊氏对「轮回说」,又开始产生怀疑了。在熊氏的观念中,认为佛教的「轮回」理论,是建立在「一切有情之生命,各各无始无终」的各自「回脱形体之神识」上。亦即,每一「轮回」的生命主体,都有各别的神识,此神识在全体生命中,是「独立」的,不因局部机体的割裂而分散。例如人之神识,不因一腿折断,而消失一部份,「以每一物之神识,必不随机体割裂而分化故」也。这样一来,在熊氏的预设中,即有一疑问出:假设神识是无量的,「遍满宇宙」,则将会造成任一机体去一部份时,即有其他神识附著其间,成另一机体者。如植物或下等动物,将其肢体切为数段,则每段皆成独立之生机体。而原非寄托神识的局部生机体,如今已为拥有本身独立之神识矣!「轮回」之每一生命各配独立神识之原则,顿遭破坏矣。熊氏如此解释,可谓对佛教的「轮回」理论的一大误解。根据佛教的「业感缘生」理论来说,「神识」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行为和意志交互作用下的一种「残余影响力」,这种「业力」,要看行为的主体如何行为而定。亦即「轮回」的业感,并非无因或偶然的,而是关系著善、恶业的影响。因此,在业力的转换之间,跟前後阶段的行为结果本有一种「函数」的因果关系。所以像熊氏所说,有无量神识,可任意飘浮、依附的情形,是不被允许的(注85)但是,熊氏却依赖如此的推测,而摆脱「轮回」的信念,转为强调,无轮回之身」的独特价值和优美的生活意义(注86)。在思相上,他也放弃了护法一系的唯识论,改作《新唯识论》(注87),主张「众生」「实体」为一源。他还说柏格森,是以生物学为证,说明此义;他则反求诸心,见得此意。又引王阳明《大学问篇》:「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说:「岂唯大大。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理由是:我与万物痛痒相关,「是无形骸之隔,物我之间」,故万物应为一体同源(注88)由此看来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仍是逻辑推论下的产物,仍可据以分析其内容,故其知识上的错误,亦随之暴露无遗!但读者中,恐仍有对其思考方式存疑者。兹再引同书的一段熊氏自白如下:
「自省思虑不易放下,或发一问题不得解决,即留滞胸中,左右思维,旁求之事事物物,冀得其徵。然理之至者,非可离於事物而求之。更非可泥於事物而求之。人但知不可离事物而求理,恶知其不可泥事而求理哉。吾尝因一疑问,多端推徵,往复不决。心力渐疲,而游思杂虑乘之以起。然有时神悟焕发,不虑而得。亦有推徵既倦,不容不休,久之措心於无,忽尔便获。更有初机所遇,本无差谬。後渐推求,转生疑惑。旋因息虑,偶契初机。总之,穷理所病,唯一泥字。......泥者,全由吾人在现实生活方面所有知识,早於无形而深远之途径中组成复杂之活动体系,为最便於现实生活之工具。此工具操之已熟,故於不可应用之处,亦阴用之不觉。此所以成乎泥,而真理之贼也(注89)。
这一段话,亦只说灵活运用思考法之意,至多应用了潜意识或直觉,与禅定体验无关,也不是不可理解者。故他要人默思冥会本不为经文所累本亦只限於「灵活运用」之情况下,方能生适当的效果;否则何能靠主观之体会,便欲服人之口?问题是:熊氏喜用此法。例如他亦曾讥方东美先生「随在儒佛书中名言转来转去」为「可怜」;引来方先生的反唇相讥说:「若涉猎佛书册而抹煞其义,横生误解,不尤可怜耶!」方先生还大加暴露熊氏思想深入「宋儒圈套」的「混语」与「遁辞」(注90)。如此激烈地反驳,是发生在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比吕澂与熊氏的论学,尤早数年,读者可以参看。研究熊十力的郭齐勇君,对方氏此文,似无所知,故稍介绍於此,以见熊氏论学之惯技,和惹人反感之一斑。
吕澂的反驳(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
吕澂在回信中,指出熊氏意见虽多,却未针对问题而谈。足见熊氏反己工夫,「犹未免浮泛也」(注91)。接著吕澂将自己数十年为学的作了一深切地回顾说:「平生际遇,虽无壮阔波澜,而学苑榛芜,独开蹊径,甘苦实备尝之。......刻苦数十年,锲此不舍者,果无深契於性命,而徒寻章摘句之自娱乎?弟切实所得处,殆兄所未及知。」(注92)然後他指摘熊论五点不当之处,证明其说,不过为「时文滥调」而已!吕澂指摘的五点中,前二点较无关紧要,只是说熊氏之学曲意顺从俗见,却动辄与人立异,故为学之发韧和讲学之居心,均有不当(注93)第三点,是批评熊氏对空、有区别的误解。吕澂说:「佛宗大小派分离合,一系於说与分别说」;并解释其观点的涵义为:「有部之宗在一切说,大众亦有分别说矣。《瑜伽(师地论)》解空,在分别说,则不得泛目为有宗矣。若是等处,岂容含混?(注94)吕澂,他认为熊氏的说空说有,是被「章疏家所蔽,充其量不过以清辨旁宗上逆般若,(圆)测、(窥)基涂说,臆解《瑜伽》(注95)。故真有真空,熊氏并不清楚。按:此段文字,吕澂後来在著信中(复信第七)仍有讨论,暂不多加说明。至於文中提到的「说一切有部」和「分别说部」,则要涉及到部派佛教的分化背景,若要在此详说,势所不能。兹引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注96),所整理的一张表,以示宗派状况(注97):
但从此表,仍看不出吕澂所说「大众部亦有分别说」的部派。希望对此阶段历史较熟者,多加指教!吕澂批评的第四点,是认为熊氏对「工夫」的看法,「极欠分明」。在吕澂看来,熊在前信中,要人「须识得实相,然後净种从自性发生。」又云:「入手不见实相,则净种非自实相生。」然而,熊氏却未说明:此识此见,从何而来?前後引生,如何结合?因此,熊氏「非薄闻熏」,即空说。──为什麽吕澂要指摘这一点?吕澂说「胜义而可言诠,自是工夫上著论」。换句话说,既然真理可以被诠释,则如何认识的方去论,是不能缺少的。熊氏在认识论上,既未清楚交代,则要他人「须识」,即无从落实(注98)。第五点,吕澂问难说:「既不能辨自说之不同伪书,又不敢断伪书之果不伪,更不审鄙意与尊见究竟异同,荧惑游移,所守者何在欤?(注99)这是因吕澂视伪书为熊氏思想之同调者,故步步进逼!其实这几点的核心,依然是针对「性寂」与「性觉」的根本异同,提出质疑。吕澂的见解如下:「一在根据自性涅盘(即性寂),一在根据自性菩提(即性觉)。由前立论,乃重视所缘境界依;由後立论,乃重视因缘种子依。能所异位本功行全殊。一则革新,一则返本,故谓之相反也。」在吕澂的看法里,「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性寂」即其「正解」。他解释说: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此即「境界依」的进路。「性觉」在吕澂看来,是「望文生义,圣教无徵,讹传而已」(注100)(同上)。何以吕澂坚决地要拣择这一区别?他认为:中土伪书,从《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传,都是由「讹传」的「性觉」思想形成的。这种「返本」的错误思想,「混合能所」,「不辨转依」,使佛教趣「净」或「寂」之途径,为之晦塞了。他又重提前信中的「性寂」问题说:「从性寂立言,故谓在工夫中所知是实相般若,此即自性净心,亦即虚妄分别。《般若》「观空不证」,《楞伽》「妄法是常,圣人亦现」,均据此义。(证则真现而非妄,常故妄现而非真,其义成也。)能知由习成增上(强化),所成所增,种姓本住,又奚待言?然习起知归(归趣般实相),无容先後也。」(注101)──这是吕澂认为符合《瑜伽师地论》正宗的看法。是他「心教交参,千锤百炼」所得来的,有亲身体会的深刻经验在,并非如熊氏所说,单是「治经论」而已!信末还说,「师新逝,不忍见异说之踵与,疑斯文之遂丧,故竭疲惫精神以呈其意」。「依止吾师(欧阳),卅载经营,自觉最可珍贵者,即在葆育一点『存真求是』之精神。......今後此种精神一日不亡,即内院命脉一日不绝。然桐鼎一竿,其难可想」(注102)我们在此可以感受到中国近代佛教学者中,极其动人的求知求真之情操。他的反驳熊十力,是否有理?可暂置勿论。但此种维持知识尊严的风范,的确值得效法!
熊十力的再次答辩(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
熊氏的再次答辩,按吕澂批评的五点,一一疏解。双方的论辩,既有共同的焦点,攻守之际,遂逐渐深刻化。由於熊信全文甚长,此处仅摘述其各项要点,无太大意义者,即省略不谈。第一点,熊氏答辩吕澂对其论点,指为「时文滥调」,提出说明。熊氏认为在议论中,应用诸如西欧学人所用如本体论、宇宙论、玄哲学等名词,是以言应机喻人,在沟通思想时,须用的媒介。儒、佛书中,虽无此名词,而不能谓其无此等意思口例如佛家唯识论系统,有无著的《摄大乘论》,成立「赖耶」(第八识),含藏种子,以说明一切「相见」,即相当俗云「万象」,分明是有宇宙论。在熊氏看来,「宇宙」即「万法」之都称,「实体」亦「本体」之异语。总之,佛书中,其归宿处,虽有不言宇宙论、本体论,其实即其关於此方面的见地如此。若说天下有一等学问,与宇宙论、本体论等,杳不相涉,在他是认为「不能想像此等学问,究是讲个什麽」(注103)?第二点,熊氏说不清楚吕澂所言何指?他说:「人各本其一生之经验,以体究道理,则宜其所见有不能无异者矣。然自性涅盘,众生共有,则宜其所见有不能无同者矣。有异则相非,不非,无由见异。来书责以不敢相非,是於拙未尝立异也。何乃以此见责耶?」(注104)--此答辩,最後一句,应是反嘲。试想熊氏如何不知吕澂责他立异说的指涉?通篇不都在辩驳「性觉」与「性寂」之别吗?第三点,是关於印度佛教史上的空、有之别。非精通佛教文献学和思相脉络者,不易厘清。其难不在义理之复杂或深奥,而是在史料的验证,须得找到出处才行。否则即不明对方所言为虚?为实?熊氏说他平日用心,不在这方面,因此对「一切说」与「分别说」的「离合之迹」,他不欲深究(注105)。在信中,前後二次(注106)提到,愿请吕澂将其撰述出来。故熊氏对吕澂的此点指摘,只有说:他在书中(案即《新唯识论》),谈空是依《大般若经》,谈有则据《摄大乘论》和《成唯识论》,自信并非无据(注107)。其他就谈不下去了。第四点,是就「闻熏」的入手问题,有所答辩。这也是双方最针锋相对之点。熊氏认为「胜义而可言诠,自是工夫上著论」一语,他可以同意。但他认为「用工夫的」是「本心」;而「本心」即是「实相」。他说:「识本心的,即是本心自识,......见本心的,即是本心自见,......本心与工夫,非是二物,如何说关合?」并批评唯识家以「赖耶」为「主人公」──流转的主体,却不肯承认「自家真主人公(本心或实相))明明存在,而唯是「染分」,教人靠经论做正闻的薰习。因此,「工夫做到熟,也只是义袭而取」(注108)。按佛教的「心性本净说」,由来已久。在早期的经论里,「心」、「识」、「意」三者可以通用,也可以依用语习惯的不同,作不同的诠释。《杂阿含经》说:「彼心、意、识,日夜时刻,须臾转变,异生异灭」(注109)。主要在说明内心有迁变生灭的无常现象。为了对治这种心识的「瀑流」特性,修行者要习禅定工夫,《杂阿含经》卷四七(注110)说:「心则『正定』,尽诸有漏。如巧金师、弟子,以生金著於炉中,增火:随时扇□,随时水洒,随时俱舍。.....如是生金得等调适,随事所用。」《经》上以炼金为喻,说明心是要调适的。如此作法,用意何在?因内心的统一、调适,可灭除烦恼,对众生的解脱--摆脱烦恼--是有效的,故《杂阿含经》又说:「心恼(染)故众生恼(染),心净故众生净」(注111)。心的问题,逐渐从「对治」的功效中,察觉到「心」之「净化」的本质问题。南传的《杂阿含经?增支部》(注112)即已讨论到「心性本净」的问题了。如说:
「比丘众!此心极光净,而客尘烦恼杂染;凡夫异生不如实解,我说无闻异生无修心故。比丘众!此心极光净,而客尘烦恼解脱;有闻圣弟子能如实解,我说有关圣弟子有修心故。」
这种看法,也是根据佛法,修习禅定有成就後的「经验报告」。对治烦恼,而使心明净,原是由工夫而生境界的发展过程;然自心可明净的角度言,当然心本身具有这种可能性,否则如煮沙不会成饭一样,是不可能有明净的成就的。--「心性本净说」,以後即成为部派佛教中,重要异议的思想问题(注113)。大乘佛教开展後,三系思想(般若系、瑜伽系、佛性系),也是就这一思想作不同角度的诠释。但,未有如熊氏所说,将「实相」、「本心」和「工夫」都看成一味的观点。假如这样的一元化,会使学习方法和作用,无从著力。起码熊氏一生的著述,要说服「读者」即成多余。更何况,他自己早期原经历了种种思辨工夫,才形成一套看法,如何可将「工夫」和「本心」混为一谈呢?第五点,是吕澂责熊氏对《起信》、《楞严》等「伪书」的问题其思想根源辩护。在吕澂看来,二者是二而一的。熊氏却绝不承认。他首先说,他的平生所学,有《新唯识论》在,与「伪书」毫无关系。又说一生为学的兴趣,「本不属考据方面」,他不必定要对此有所评断。可是在吕澂节节进逼下,他亦忍不住说;下述的看法:「《楞严》一书,颇有不类佛语处。然以文体论之,其浩衍、雄浑、决非中国人所伪。......当是印度外道之归佛者所为。」《起信》中,唯生灭与不生灭和合一语,绝不是佛家旨意。.....除此之外,综其大旨,不必背佛法也。《圆觉》以文体论,当是伪。然若以谈性觉而非之,则菩提是佛说,其可病也?」(注114)但是这种讲法,非文献学精密的考察,只以本身思想立场衡准之而已!在熊氏的意见中,仍然强调「说自性涅盘者,只形容自性寂的方面。说自性菩提者,只形容自性觉的方面,断不可因此硬分能所也(注115)。况且,吕澂既主张「自性涅盘」是「所缘境界依」,其中显不容著力;而佛陀总劝人发「菩提心」,分明是在「自性菩提」,即「性觉」上致力。--如此,则在各人的立场上讲,只能是相对的正确。判「性觉」为「伪说」,「伪说」未必不可尊也。这是熊氏一直坚持到底的!至於生平「任情直行」之病,熊氏也不否认。但总以真理为依归,求诸心,信诸心,而後即安,「则一生之所持也」(注116)。
吕澂对前信的补充说明(复书三)
在熊氏回信之前,吕澂又补寄一信(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即在原信「能所异位,功行全殊」的句下,加注「一则革新,一则返本」八字。按:此八字,熊氏在回信时,显未看到,故信中不曾提及。现在我们看到的信函内容,是後来才补上去的。吕澂认为这八字,可当「眼睛」,使意义显豁。并且他又加了一段重要的说明:
「唯其革新,故鹄悬法界,穷际追求。而一转捩间,无住生涯,无穷展开。庶几位育,匪托空谈。此中妙谛,未可拘拘本体俗见而失之也。唯其反本,故才起具足於己之心,便已毕生委身情性,纵有安排,无非节文损益而已。等而下之未至於禅悦飘零,暗滋鄙吝,则其道亦既穷矣。」(注117)
按:吕澂在这里,诠释两者的区别,是所谓「瑜伽正宗」(注118)的禅定理论,摆脱中国式禅宗的立场,恢复了印度禅法的风貌。此话怎说呢?因吕澂在前信解释「性寂」中的「工夫」时,曾提到「实相般若」即「自性净心,亦即虚妄分别」。又补诠说:「证则真现而非妄,常故妄现而非真,其义相成也」(注119)。──确为唯识学修行理论的中肯讲法。如果不懂,即会对其所述的概念名词,产生一些望文生义的联想。在佛法发展的思想源流里,常有理论影响实践,或实践修正理论的状况出现。唯识学是由修习禅定的体验心得,逐渐发展为精密的理论体系。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是认为人有「无明」,障碍了「智慧」,因此有种种错误的行为产生,并造成一连串不良後果的影响──业感缘起。为了要透视这一错误的根源,又能进而消除它的不良影响,豁显真理的光辉。於是要依止观的修链,而逐渐接近到解脱的境界。解脱的境界,难以形容它有什麽内容,只能说它是烦恼作用止息的境界。「寂」的意思,就是指这一境界。用譬喻来说,就像乾净的水,完全透明,无一丝杂质,或像白光一样,没有一点黑暗的成份。但是,要达到这一步之前,必得先克服认识上的层层障碍──妄识乱现。这就引发了唯识学的认识论问题。到底在主观意识影像背後,有无一根本的源头呢?从经验上,我们知道,感官接受的外界讯息,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对外界的认识也印象迁流不定,所以无从掌握一不变的「真实存在」。但是,从内者上,透过禅定的作用,使感官的认识规律化,向内层层探索,直到一切意识的乱流被止息了,心的作用纯粹化了,於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离间的距离消失,这样就变成一纯粹的境界。吕澂在前信中说:「证则『真─现』非妄;常(出定的情况下)故『妄─现』而非真。」的确是一种「境界依」。然而,为何说是「革新」呢?「革新」是对克服妄识而言。禅法的止观成就,是有阶段性的,并非一悟即成。在达到「鹄悬法界」──净化、无烦恼、完美的顶点──之前,确需「穷际追求」,妄与真之间,成了一彼消我长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些体验,虽然一般修行者,也能从静坐中得到一些;但佛教是以佛陀的禅观为典范的,故非浅尝即止,也非无圣教依据的。假如能明白这一道理,美好的人生目标,便可任尔追求。一旦禅观至最高境界,则「位育」──借用《中庸》的概念名词──就不只是空谈的理论了。因此,吕澂会向熊十力表示,他「所得者,心教交参,千锤百炼」,绝非熊氏想像「治经论」三字便可了事。我们固无从衡断雨的境界如何?但其说词符合佛教经论,则是没有疑问的。
熊十力对吕澂补充说明的酬答(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於吕澂的问题补充,已缩小为关於修行理论与实践境界的说明,意见集中,熊氏似可以扼要酬答?想不到,熊氏却洋洋洒洒,回了数千字。熊氏的信虽长,论点却不多,归纳起来有三点:1.认为吕澂讲的「鹄悬法界,穷际追求」,是向外的。如西洋宗教家之於神帝,即悬以为鹄而起追求者也(注120)。2.由於认为吕澂是向外追求,不知返本,固有外羡情生、祸几且伏的种种流弊。熊氏认为其《新唯识论》是讲本体,举体成用,即用见体,故体用不二。然自体显用,即有分殊;分殊既由体化,便具有一一大全的本体。只要返本见性,即可源源显发德用,不断创新。如照吕澂所说,向外追寻,即受拘於外物,本体终不能自显。是故返本之学,由顺天(本体)而自强,修之既久,工夫纯熟,本体全显,即天人合一矣(注121)!三、对自己无下学工夫和任气使性的「内疚」。由於熊氏一向自尊心极强,此种语气很不常闻,特摘录於此:
「吾(熊氏)内自省,一向没下学工夫,玄思妙悟,只以粉饰胸间杂染,转增罪过。年垂六十,如何再不回头?外观常世士习,几不见有生人之气。尤伤族类将危。吾老矣,念挽此危,唯有对人向日用践履处提撕,使之敛其心於切近,养其气於平常。从下学立得根基住,久之,资美者,自悟胜远事,而何待予为之强聒也?吾四十五以前,犹甚使气,四十五以後,每以此自愧,宁避人,无斗口,然只强抑,非真能无竞也。一矜字,尤去不得,下学工夫甚不易,注意及之,而後知其难也(注122)。
按:此处下学工夫,应包括二方面:一是扎实的学问基础,二是切实的修养工夫。熊氏在信尾忽流露此种语调,是认为吕澂要他,鹄悬法界,穷际追求」;然对他而言,平生正犯此好高心的大过,故引以为戒。──照此看来,他实不清楚吕澂的语意,也非故为扭曲对方的观点。而是他根本不在此思想路数,也无真正禅学的修持经验,宜其讲话不对头也。
吕澂对熊氏近两次答辩的再澄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吕澂在信中明白指出,他之与熊氏的论本是取准於佛教理论的对否?而非讨论熊氏《新唯识论》的思想。又说他信中,「只说鹄悬法界」,哪有一定在外之理?新近一函,更补充说明:「归趣本不外求」(注123)。然而,他最重要的一段,依然是强调「性寂」和「性觉」,是对「心性本净」说的两种解释。两者,一直,一伪,各有其整个意义在,不能以「一心开二门」的观念,粗糙地理解。最後,他说西洋人谈小乘佛学,常谓其不涉宇宙本体论,却不以为不能想像。而相对佛学的看法,本体论实是一种「俗见」──世间学问的观点(注124)。
熊十力对吕澂澄清信稿的异议(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当吕澂强调他的「鹄悬法界」,是对内,不是向外,并且取准佛说之後。熊氏面临一个难题:他不能再以自己的返本论来驳对方的外寻论。因熊氏坦言:「於佛说,始终作为一种参考而已。完全取准,问之於心,确不能承受(原注:只是不能完全也,非全不承受)。」所以两人并未在一共识的基础下─完全取准佛家理论──展开讨论。
熊氏凭记忆中的佛学知识(注125),来解他所说的「本体」,即佛书中所云「法性」耳。他认为西洋的心习,虽治佛学,不足以判断小乘的「法性」,是否未见?他个人所言,虽本大乘说,亦仅就所知者言之,其不知者,固未尝言也。但「本体」并非俗学,和佛书常见中的「实性」、「实相」,其实是一样的。在佛典中,也有名词和世间相同,而解释相异的,可见名词之通用,也是没有不可以的。准此以谈,熊氏相信他的《新唯识论》,谈本体呈现、大用分殊,是不外於本心──本体──的。他对吕澂所说「性寂」、「性觉」,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评前者为「真」,後者为「伪」,是有怀疑的。最後,他仿效禅宗语录的口气说:「吾以为须勘起的是谁?果何所著?若得主人公,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起即无起,更无所著也。」(注126)熊氏在此异议信中,全采守势,已没有前此各信中的飞扬议论了。但他仅堪自辩的「本体」与「实相」两者同其指涉的说法,有无可信度?如有,依据何在?──这是熊氏在信中遗下未解决问题。
吕澂驳熊氏视本体与法性为一的看法(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针对熊氏的自辩,吕澂随即提出反驳,并一再嘲笑熊氏对佛教理论懂得少。吕澂的语气,可从下述摘录看出:
「前函结束所谈,而来复邀勤,获求一是,意甚可感。惟兄所知佛说太少,又久习於空疏,恐区区文字之真,亦唐劳笔札,而终无益於介甫也」(注127)。」「前函往复,皆从闻熏一义引起。所辨皆佛家言,不准佛说,讵得是非?乃足下一见佛字,即避之若□,以自绝於入德之门,此可谓大惑也。」(注128)「足下谓就所知以谈佛学,此自是要好之意。但前後来信,强不知以为知,其处亦太多矣(注129)。」「尊论漫谓佛家见寂而不见化,此咬文嚼字之谈,岂值识者一笑。....足下乃即凭此等肤见,横生议论,侈言会通。瞎马深池,其危孰甚(注130)!」
但是,吕澂有何自信,可以如此讥嘲熊氏?由於熊氏在信中随口谈及小乘对「法性即是本体」亦有所见,被吕澂抓住错误的把柄,遂脱身不得。吕澂不客气地的驳斥熊氏的看法,「纯系臆谈」。他说:「法性共相,不可作本质观(注131)。小乘更用为通则、习惯,及自然规律等义(注132)。彼於法性有证,则唯证此而已,岂得视同本体哉?(注133)」此等文献学的训诂,熊氏生平未涉此域,实无从讨论起,辩论的优势自然落入掌握中。但何以吕澂在此处提出的证据,较前数封信,更具信服力?因佛教经论中译後,语尾的词性,很难找到全然相符的中文来取代。但如对勘梵文或巴利文原典,则原义词性为何?便清晰可辨。吕澂在原典语文的条件上,当代治佛学者,罕有人可比,熊氏不能说无闻,故一旦涉及原典文献,除了谨慎处理,不多生议论外,别无他法。不幸,他喜欢拿「本体」到处比附,遂容易错看法。此项毛病,在大乘佛教思想中,因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的真妄说,几同时存在,谠同如藏思想的「性觉」说,还可在经论中游移,假如追溯到原始佛教或部派佛教的范围,便须视各派的传承说法来决定了。──熊氏事实上是因谈超过了自己知识领域的东西,才被逼得无招架之力!吕澂一击中的,便再展开对熊氏以「本体说」比附佛说的批判。他说:在中译经论上,有实相、实性之词,皆就「相」言,不可因其译文上有一「实」字,遂漫加附会。他从佛教的解脱思想来看,认为是重在离染转依,而由虚妄生实相(原注:所谓幻也,染位仍妄),以著工夫。故立根本义为「心性本净」。「净」者,是指妄法本相,非一切言执所得扰乱(注134),此即「性寂」之说也(注135)。但「性觉」与「性寂」的区别,是否更有不同之处? 吕澂补充说:自性涅盘,法性法位,不待觉而後存,故著不得觉(注136)。──根据这一见解,吕澂检讨了六朝时期「讹译」的问题。他说:「六代以来,讹译惑人,离言法性自内觉证者(不据名言,谓之内),一错而为自己觉证,再错而为本来觉证。於是心性本净之解,乃成性觉。佛家真意,遂以荡然,盖性寂就所知因、性染位而言,而性觉错为能知异性已净。由性寂知妄染为妄染,得有离染去妄之功。但由性觉,则误妄念为真净,极量扩充,乃益沈沦於染妄。两说远悬,何啻霄壤?然性觉固貌为佛家言也。夺朱乱雅,不谓为伪说?得乎?知为伪说,不深恶痛绝之,得乎?(注137)」
既然「性寂」和「性觉」,是如此的截然相异,吕澂遂不客气地说:熊氏的「本体论」,是揣摩本体,以迎时好,乃是不折不扣的「曲学」。他甚至建议熊氏说:「戋戋《新论》,能博得身後几许浮名?敝屣弃之,又何恋哉!(注138)」
熊十力回信谈辩论书信的处理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熊氏在信一开头,即承认吕澂的读书多於他,但他对「性觉」的道理,自有真见处,自信依然是有的。但觉得「性寂」、「性觉」之辨,是一至要的学术公案,他希望将双方书信整理,集入《十力语要》篇三。问题是:熊氏声称要将吕澂的来信,「字字句句均不敢删,以存真面」(注139);又说不标明吕澂之名,是考虑欧阳既逝,两人之诤,会被僧人讥笑(注140)。此种说法,不知吕澂能接受否?
吕澂不同意熊十力的作法(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三日)
吕澂接信後,认为熊氏前寄各信,并未接受他的意见,编入《十力语要》,乃属多余。如果定要编入,则请附录吕澂各信全文,不要改头换面。──熊氏虽在来信中,亦附有信稿,但非附录全文。──因此,他认为熊氏割截其信首尾,致意义不明;又将最初一信,原是由批评欧阳偏重闻熏一义而起,改作为针对《新唯识论》而发等,是作伪:自欺、欺友、并欺世人。他叹息熊氏原先各信,都能流露一种心平气和的论学态度:对吕澂所说有「过分处,皆轻轻带过」;「又自表白昔日玄思粉饰之非」,态度之佳,为数十年所未见(注141)。如今改造信文内容,可谓一转念间,将真诚流露处,一概抹煞,....(注142)。
熊十力对吕澂指责意见的申辩(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熊十力在回信中,先提吕澂在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那封信。他对吕澂引《巴利文字典》谈佛家小乘法性义之事,仅表示「吾决不能赞同」,便交代过去。又说如《阿含》、《俱舍》等,过去所阅者,如今已不能记忆,故「暂不答」。─换句话说,他与人论学,可不翻阅参考资料,仅靠记忆与否,来决定谈与不谈。这种方式,也许他已察觉并非十分妥当,因此在信中表明自己「素性急,凡来书,往往立答,自不必尽意也」(注143)。他说梵文明净,中译清净,不得谓之错。他举《诗经》:「会朝清明」。《礼记》:「清明在躬」。清明连用,岂有清而非明者(注127)。──这样的语源讨论,涉及到的,只是中文语意的问题,梵文的词性如何?仍未解决。
但熊氏的信中重点并不在这里。他最在意的,还是吕澂说他改造信件,是自欺、欺人、欺世的恶行。他的答辩是:另有原因(详後),故有说不周全处。如今前後才月余,自行改定,又寄请吕澂本人同意,实不应以伪作之罪名加之。如吕澂反对,他当遵嘱,不必编入《十力语要》。他说吕澂的信,如要发表,除四月十三日谈「鹄悬法界」那封外,皆保存著,也不难录出(注145)。接著,他解释割去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份(注146)。但此事,在吕澂看来,并非如此单纯(详後)。按:在现存一九四七年版的《新唯识论》,卷下之二的〈附录〉中,依然是改造的信文,而非原稿,连吕澂之名,亦未附上。可见熊氏未尊重原作者意见。不过,熊氏对回信太快而致言不能尽意的原因,提出二点说明,不论是否有理,颇能代表他的此时心境,故摘录在此:
「昨腊鄂东寇祸,久不得家信,必乱甚。」「竟师新逝,知足下(吕澂)悲苦中,故於来函之骄横无理(原注:须知吾於此理自有真见),一概避让,不愿针锋相对,冀足下稍悟也。矜心胜心,皆所谓杂染。潜玩玄文,而未离此杂染,乃哀之甚也!前自抒所感,亦冀足下有同感也。人生已至五十、六十,更有许多岁月,何苦如斯?足下骄傲之气,溢於文墨而不自觉。盖天下地上,唯我独尊。其养之有素,则不自觉,宜矣。(注147)!
显然对吕澂咄咄逼人的语气,表示了情绪上的反弹,不知吕澂如何作答?
吕澂最後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吕澂接信後,也先回了一段感性的话说:
「得复颇有所感。前寄各书有激切处,大抵出於孤愤之怀。十余年间,自视□然,不敢於佛学著一字,复何所骄於故人哉!内法东来千载,只余伪说横行,流毒无尽。自审良心犹在,不忍□然。偶触尊函,抒其愤慨,岂以虚矜求胜於足下乎(注148)?」
信末又重复提了一段:「惠复寄慨於年将六十,来日无多,凄动予怀,难能已已。足下自是热情利智,乃毕生旋转於相似法中,不得一睹真实,未免太成辜负。故为足下累牍言之,不觉其冗长也。否则沧桑任变,不为君通,又何碍哉?区区之意,幸能平心一细察之(注149)。」
吕澂的著眼点,是佛法的根本精神何在的问题。在他看来,熊氏的思想,只是伪说流传下的枝叶,揭其缺失,确属菩萨心肠力一片关注的好意。但,他和熊十力都很难让对方接纳己见。因彼此的思想取径,截然相异,毫无妥协的余地。故吕澂在礼貌话讲过後,仍再度展开对熊氏的论点的全面批判。吕澂批判的,是熊氏的改作稿。但改作稿是否如前述附在《新唯识论》卷下之二〈附录〉,则不得而知。不过吕澂在此信中,又提出熊氏不当之点,达十余处之多,除思想讨论之外,尚批评了唐代译经不精确的问题,充分展现了他在佛教文献学的版本与译语方面的特长。以下就其指摘熊氏各点,稍加讨论:1.吕澂认为「辨空有」的问题,汉译的小乘典籍最齐备,「经具四含旧文,律备五家广本,论有毗昙两类,始末灿然,较诸锡兰所传经论,改文而又残缺者,所胜多矣」。而熊氏以为「鳞爪未完」,是错误的(注150)。2.龙树、无著之学,後先融贯,「两家皆对一切有而明空,皆对方广道人而明中道空。不过一相三相,後先为说方式不同而已。熊氏据「清辨立说,强分空有」,是错误的。按:吕澂在此对「空、有」的区分,是以部派的佛教思想来立论的(注151)。大乘思想中,空有之分,以「中观」代表空宗,「瑜伽」代表有宗,当代印度哲学家C.Sharma的区分,则是(一)、空宗,(二)、唯识宗,(三)、自立唯识宗(Svatantra-Vijnanavava)。空宗以龙树为代表,自不待言。唯识宗外,又分自立唯识宗,则是国内佛学界较罕听闻的。其实前者是指无著、世亲一系;後者为陈那、法称、莲花戒一系,即逻辑学派的唯识论(注152)。可见就思想体系来看,是可区分的。但吕澂之说法,亦不算错,因就佛法的缘起论来说,瑜伽、中观都堪称正宗注释,只是著重点不同罢了。3.吕澂指摘的三、四两点,是认为龙树兼主《华严》,非单宗《般若》;无著通《般若》、《宝积》,非专主「六经」(注153)。因此,熊氏看法为误(注154)。按:唐代发展的唯识宗,有所谓立宗的「六经十一论」。「六经」即:《楞伽经》、《阿毗达摩经》、《华严经》、《解深密经》、《密严经》、《菩萨藏经》。「十一论」中,以玄奘译的《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二论为根本。吕澂如此指摘,除了文献典据之外,最主要是想针对佛法的解脱之道,重显正统缘起说的中道思想,纠正「性觉说」的长久流弊,因此力言「中观」与「瑜伽」的共通点,而少言其相异点。4.吕澂认为大小乘思想,以「一切说与分别说」对抗分流,是学说上的实质差异问题,而熊氏仅视为「流别」,是不当的。他的理由是:「佛说归於分别一切,有宗故意立异,所目佛说,意义遂殊」(注155)。按:「吕澂在一九五六年时,曾撰文补充了这方面的内容,他说:「有部的重要学说,即以《大毗婆沙论》为中心......。......从《婆沙》极其繁复的论题里,可以提出最基本的一个论点,即是『有因』。有部的主张一切法实有的最後根据在此,......」「本来佛家学说和别宗最有区别之处,为说因善巧,能离开无因论、不平等因论,而以独到的「缘起说」为中心,有部对这一层特有发挥,所以偏得「说因」的稍号。另外,说一切有这一命题,包含有一切法有和三世有两个部份。对有部外的各部说,......只是过去未来的有不能得到共评,......」(注156)。根据上述说明,可知吕澂论述下的「有部」,是指解释三世一切法有时,与他宗不同的「说因部」,而非「瑜伽」与「中观」之分的「有宗」。5.吕澂认为「性相」之称,如同「考老」转注。例如「三自性」即「三自相」。而熊氏以之附会「本体与宇宙」,是不可以的(注157)。又说:无著据《瑜伽师地论》以谈「境」,详其所著《显扬圣教论》。因《显扬圣教论》以「二谛开宗,无所不包」,世间出世间的层次可以融通,而熊氏以为「谈境莫详於《摄论》、《唯识》」是不对的(注158)。--尤其《摄论》和《唯识》是依《毗昙经》,与《瑜伽师地论》异说,如「本地分」依圆染净相对而谈;《毗昙经》始说依他二分。熊氏错以为《摄论》和《唯识》两论,悉据《瑜伽师地论》,是不应该的(注159)。6.吕澂为了追踪熊氏典据错误的来源,更上溯探讨唐代的翻译的问题。这是他多年来的治学兴趣所在,其熟悉的程度,自不待言。他说窥基纂集《成唯识论述记》时,「淆乱之家,迷离莫辨」。例如误安慧说为难陀说,又以胜子等说改护法说。这些错误,如今有安慧的梵文本与护法论净译本,可勘证;圆测的注解,错误更多。--此二家为熊氏唯识知识的来源之一,源头有误,熊氏之思想自失其正确性。吕澂不只批评基、测二人的缺失,更批评玄奘的译文,「喜以晚说,改易旧文,谨严实有不足」。他举的证据如:以《瑜伽》说改《般若》,常见「唯心所现」与「无性」为「自性」之义。又以《毗昙经》改《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而有言说「性」与「离言性」平等平等之义。又以惠护「遍计执余」之说,改《摄论》;以清辨「和集说」改《唯识二十颂》;以护法「五识说」改《观所缘论》,几於逐步移观,终不以完全面目示人(注160)。
故吕澂断定奘译为不忠於原本之意译,使唐人译语面临大冲击。--因他在「内学」年刊第四辑,已论过此问题;并且於一九三六年,有奥人李华德洞究梵本的《唯识二十颂论》与《宝生论》,赞服其说不已(注161)。於是他相当有自信的提到:俄人刚和泰虽曾与黄树因对勘过藏文的「摄论」,认为奘译可信;但如其未死,而见吕澂之发现,亦必肯认。(注162)。7.从唐译本揭露了熊氏的知识来源不可信之後,吕澂正式批驳《新唯识论》的典据问题。熊氏曾说无著「三性说」,为引据《大般若经》而更张原意,所以「三性说」是始於空宗。吕澂从版本学的立场,指出熊氏见解的「无稽」。因熊氏所说的无著引据《大般若经》,实是晚出的〈慈氏问品〉,为瑜伽系所宗,和空宗是无关的。为何无关呢?吕澂说,鸠摩罗什译的《大品般若经》不载此文,梵本与藏译旧本《般若》亦无此品,乃至奘译无性的《摄论》,引用经文者,西藏译本亦不见有,可见其流行甚晚。在西藏《大藏经目录》亦谓:龙树於龙宫所得《般若》,亦无此品。证明非龙树学所宗也。并题名「般若」者,皆空宗所专有,即不可一见「般若」,即目为空宗之说。他指责熊氏不辨双家思想之不同,而「遽为是非曲直之判决书」,不足以服古人之心,「又岂堪向世人而说」?「蛮横无理,一至此极」;即连其以《心经》解《般若》,也是强不知以为知(注163)。所以《新唯识论》自许为熊度谨严,实不可信也!8.吕澂最後总结他的意见为:

甲、「性觉」说由译家错解文义而成,天壤间真理绝无依於错解而能巧合者。乙、道理整个不可分,「性寂」说如觉有一分是处,即应从其全盘组织,全盘承受,决不能尝鼎一齐,任情宰割。丙、佛家根本,在实相证知,以外绝非神秘,应深心体认得之(注164)。
熊十力最後的答辩(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
对於吕澂的前述各种批评,熊十力并不接受。不接受的理由,大多依据传统的经典知识,肯定传统的说法为可信的。即或有如吕澂所说,但他仍认为「唐人相传」以龙树、无著分空有,是「成案不可翻」;或说吕澂所指的文献证据,也非一定如此。关於《摄论》、《成唯识论》谈「境」,不详《瑜伽》,他则「决不能承认者」。不过他既无工夫、无心情、又无足够的参考书籍,所以他仅凭「记忆」来谈,可是又语焉不详。他在信尾对吕澂说:总之,佛家之学,毛病甚多。我愿你照他的真相讲明算了。不必有意为他回护。佛家尽有高深而不可颠扑处,但以吾所见,其妄诞处实不少,而无著之徒为尤甚。印度人最喜弄名词,许多地方弄得甚好,其弄得不好者也不少。中国先哲最不肯弄名词,其长在是,其短亦在是。我对於佛,根本不是完全相信的,因此,对於伪不伪的问题,都无所谓。我还是反在自身来找真理(注165)。
前後双方论学,历经四个月之久,但,终究还是白讲。郭齐勇说,熊十力的此种态度,叫「王顾左右而言他」(注166)。吕澂除了将双方论学函稿,全部披露,让读者自行判断之外,又能如何呢?
五、争辩的时代意义
吕澂与熊十力的论学函稿,是在一九八四年,才全貌发表。在此之前,熊十力也以改作稿,收入《新唯识论》语体文版的『附录』中。此两种文献的问世,到底对学术界投下甚麽影响,实难断言。因为「性觉」与「性寂」的思想争辩,对未构成当代思想界,重新再检讨的大问题。研究熊十力思想的郭齐勇,曾在《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列举了「五十年来佛教界的批评」(注167),针对熊著《新唯识论》谈佛学的缺失,作了各种角度的检讨。但是,佛学方面的缺失,并不影响他在新儒家思想的高度评价。例如杜维明认为,「熊十力先生是中国当代『规模广阔,神解卓解』的哲学家。」「《新唯识论》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以纵横旁通、辨析入微的系统结构来阐明扩充体验身心之学的奇书(注168)。」陈荣捷则认为:「熊十力哲学的特徵,是把仁作为本性,把天人合一作为目的。」「熊十力从佛学中所获益的与其说是唯心主义,不如说是瞬息变化的概念。他把这运用於《周易》的生生不息的学说,并予以强化。这个能动的变化观念,在新佛学,特别是在王阳明那里,已经是显著。但是,熊十力为之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除冯友兰和熊十力以外,在二十世纪还有其他人,特别是欧阳竟无、太虚和尚和梁漱溟也企图重建传统哲学。欧阳竟无和太虚两人只是复兴唯识论哲学,而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梁漱溟给孔夫子的仁的概念以能动的直觉的新解,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则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除此而外,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哲学家影响了更多的中国年轻的哲学家(注169)。」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注170)。但是,我们要反问: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既然是以「性觉」说为主,根据吕澂的驳斥,是一伪经伪论中流传出来的违背佛教「性寂」说的错误思想,何以在新儒家的立场看来,反而是一种创见?这种评价的差异性,是因何而产生的?是否在佛教的解脱立场,被视为「不了义」的思想,在儒教的生命哲学里,恰好是一有意义的思想?假如是,那麽这代表人类的思维,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可以相对性的适用各种不同的思想?否则,「性觉」说既然可和儒家结合,是否代表儒家思想是错误的呢?在处理吕澂和熊十力的论学问题时,我们发现熊氏一直处於文献学方面的劣势状况,几乎对吕澂的一再批评,显得招架无力,岌岌堪危。但是,一转身之间,熊氏又成了新儒家的思想巨人。其评价的变化之大,知识标准的尺度游移,可以说,是思想史上最奇特难解的现象之一。问题的关键性无他,其学术逻辑建立於以下的预设:纵使熊十力在佛学思想的理解方面,是错误的,他自己体验到的「本觉」说,对儒家是有效的,故其价值可以肯定。但是,对这样的学术逻辑,是否有不同的反对声音呢?有的。方东美在〈与熊子贞先生论佛学书〉一文,曾指出熊氏不但误解佛学,连宋明理学也错误甚多,证明其对儒佛的衡准一无是处(注171)。最讽刺性的,是和他相交四十年之久的梁漱溟,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撰出《读熊著各书书後》约三万余言,全面批判熊氏的儒佛思想。梁之此文,并获当初盛赞《新唯识论》的马一浮之首肯(注172)。如今,此文连同梁漱溟之〈忆熊十力先生〉一文,皆收入《勉仁斋读书录》(注173),使梁与熊之间的思想紧张性,为之真相大白。兹摘录二论熊氏为学的话,以见一斑:
对於哲学,熊先生固自强调其有起知识不尚理论之一面,力斥知见卜度、臆想构画、一切向外寻求之非;--这代表东方说话。但同时又肯定其有恃乎思辨,而且据说是极贵玄想(注174)。这意在吸收西方哲学之长,以建立其本体论、宇宙论等的。口口声声以『内证离言』「体神化不测於人伦日用之间』为哲学旨归,而实则自己不事修证实践,而癖好著思想把戏。其势要把不尚理论著,引向理论去,而後有把戏可玩,从《新唯识论》至《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种种著作乃始有其归著处。不然的话,英雄将无用武之地(注175)。
熊先生情趣在好玩弄思想理论把戏,他也完全明白东方古人之学莫不有其反己之真实功夫为其学说所自出。不应该离开此等真实功夫而谈甚麽思想理论,而怠于反己之实功。这使开始堕落。距今三十年四十年前,其迹不显,近二三十年来,渐渐显著。这表现在他耽於著述,自得自满,高自位置上。前曾指出他『悔而不改』,已是积重难返时候。比及晚年乃大暴露:浑忘理论必出乎实证乃有其价值,而特高视理论;傲然以理论自雄,意呵斥古人,略无所谓;然其谈理则愈以泥执,一反其早年所实悟者(注176)。
对方,梁氏的这些批评,本文在前面讨论熊氏的方法结论时,亦曾交代过了。可见熊氏的思想,纵然有理论的价值,也欠实证的工夫。--而这一点,正好背离了明理学的为学立场。何况,其理论之可商榷者正多。我们对熊氏思想的评估,要自各方面来考量,否则只能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至於吕澂的思想部份,牟宗三著《佛性与般若》,亦批评吕澂的看法(注177)。并大肆发挥《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注178)。可说为「性觉」说张目。但吕澂主张的「性寂」说,则依然未受佛学界的重视。因此,要估评吕澂和熊十力论学的时代意义,我们只有将其安置在百年来的儒佛思想史来理解,才可以知道其意义在哪里?要如何定位?--对於这个问题,我将留待撰《民国唯识思想史》时,再予以处理。此时仍难有明确的定论。不过读者可在本文的争辩背景中,找到此一思想的线索。
六、结论
经过以上的各节讨论後,我们对吕澂与熊十力在论学函稿中,所争论的问题,应该可以看清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双方争辩的思想重点所在。争辩虽是因熊氏批评其师欧阳为学以「闻熏」入手,未必如宋明儒「鞭辟入理」;也不若他的《新唯识论》融通儒佛,为「东方思想的结晶」,於是,引起吕澂为维护师门而反驳「异说」。双方的争论点,遂由「闻熏」一语,逐渐具体化为「性寂」与「性觉」的诠释与思想立场之护卫。吕澂的依据,是由佛教文献学出发,循思想史脉络以谈唯识思想,肯定「性寂」为瑜伽正宗的说法。熊氏则依据本身对轮回说的误解,建立起万物一体同源的「本体论」,并将此思想比附为「实相般若」。吕澂则力辨两者思想截然相异,「性寂」为「革新」;「性觉」为「返本」。前者以「境界依」,可以为道日进,以达解脱之圣域;後者误「情性为性觉」,扩充之即成陷溺欲救,反致沈沦。熊氏则力言,见体可以天人合一,工夫自在「本体」作用中。在在肯定自己之为有所见!但是,既涉及佛教义理,衡准佛教文献证据,乃理所当然。吕澂在此表现了他的治学功力;熊氏则凭记忆印象,以论佛学。於是辩论成吕澂控制全局的优势场面!虽然如此,熊氏依然自我回护,语多遁词,拒纳吕澂意见。吕澂则不满於熊氏为传统佛学「伪书」思想张目,语气激越,再三讥嘲熊氏之「不学无术」。遂使熊氏在垂六十之年,面临最大的窘境。为维护门面,不惜改作信稿,转移焦点;却不获吕澂同意,双方不欢而散。此一辩论的结论,并未在学术界造成重大影响。吕澂迟至一九八四年,才将全文发表;熊十力则於一九四七年即改作,附於《新唯识论》,双方人格高下,由此可以看出。问题是:熊氏的哲学思想,在新儒家的阵营中,有极高的评价,造成一学术的难题:即在佛学方面失败:却在儒学方面成功的奇特例子,评价之游移,诚不易言。幸好,反对的意见,除佛教界之外,也有其他重要的思想家,如梁漱溟、方东美的彻底批评即是。两者的长文批评,有助於平衡一些学术界的奇特见解,毋宁是好事。而吕澂方面,也有熊氏高徒牟宗三的反驳,证明学术界仍余波荡漾。不过,整个问题,唯有放在百年来的儒佛思想发展史来看,才能界定其时代意义。此须等《民国唯识思想史》,才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