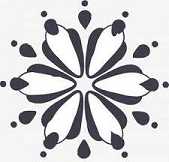电影里的西藏,只能用来朝圣吗?
发布时间:2024-06-29 03:28:32作者:楞伽经讲什么一提起西藏,人们会联想到的词大概是“朝圣”,这和影视作品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是电影里的西藏,只能用来朝圣吗?近几年来,创作者们的态度正在改变。比如最近上映的一部涉藏电影,讲的就是一个现代派的荒诞故事。
司机金巴行驶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公路上,撞死了一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羊。司机金巴因此产生了负罪感,想要把这只羊送到庙里去超度。
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叫金巴的杀手,杀手要去杀他的杀父仇人玛扎。杀手金巴在中途下车后便消失无踪。虽然司机金巴的情人认为,在现代社会,此事非常荒谬。但是,这事却在司机金巴的心中萦绕不去,他一定要去一寻究竟。一个如梦境般荒诞又充满着寓言气质的故事,就这样在高原上徐徐展开。
这是继2016年公映的《塔洛》之后,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新作。这部名叫《撞死了一只羊》的新作,除了改编自导演本人的小说之外,还改编了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在电影上映之际,我们对导演万玛才旦进行了一场专访。万玛才旦的电影主题总绕不开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身份的迷失与寻找等现代化的精神困境。从“藏地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到《塔洛》,我们能发现这种冲突越来越剧烈。这也包含了万玛才旦对藏区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和未来的思考。在《撞死了一只羊》里,万玛才旦似乎对藏区的未来有了新的期待。这一次,万玛才旦是如何书写他的藏地情怀的?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万玛才旦,中国第一位藏族导演,被中外电影界视为最重要的藏族导演。曾凭《塔洛》获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撞死了一只羊》获得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虽然《撞死了一只羊》与万玛才旦以往的影片一样,仍然以藏地为背景,但是,万玛才旦首次融入了一些类型片的元素,如复仇和杀手。在叙事结构上,万玛才旦首次打破以往顺叙的结构,中间插入回忆与梦境,并且首尾呼应,形成了“轮回”叙事结构。在视觉上,万玛才旦用了三种颜色对应回忆、现实和梦境三种不同的时空情境,并用4:3的复古画幅虚化片中的时代,增强形式感。除此之外,万玛才旦还设置了大量的意象和象征符号,营造了一个庞大的“隐喻迷宫”。
如此具有形式感、梦境感和荒诞感的影像,似乎与万玛才旦先前偏写实的影片形成了鲜明反差。从2005年万玛才旦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开始,我们就能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看到伊朗电影,尤其是阿巴斯导演对他的影响。他和许多伊朗儿童片一样,拍摄故乡小孩的日常生活,他们大多都是非职业演员。导演拍摄的方式也是半纪录式的,因为他希望通过影像尽可能地表达一个真实的藏区,而不是外人所想象的藏区。在《寻找智美更登》中,他像阿巴斯许多带有反身性质的电影一样,由一个电影导演带着摄制组,去寻找出演智美更登的演员为线索展开。我们也能从万玛才旦所带起的“藏地新浪潮”导演,如松太加和拉华加的电影里找到伊朗电影的痕迹。那么,为什么万玛才旦在《撞死了一只羊》里,影像风格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1
没有刻意地去改变风格
这跟文本本身有关系
新京报:与“藏地三部曲”和《塔洛》相比,你在《撞死了一只羊》中加入了许多风格化很强的视觉元素,形成了强烈的荒诞感。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在影像的美学基调上,从写实转变到写意呢?
万玛才旦:我以前拍的电影都比较写实。《撞死了一只羊》跟我以往拍的电影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因此,大家可能会出乎意料,觉得我好像刻意地改变了风格。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地去改变风格,这跟文本本身有关系。
这可能跟原著小说本身有关。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的风格,跟我以前创作的小说很接近。这也是我对《杀手》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当我遇到了这样的题材、故事、还有讲述方式,我就要使用一个相对应的影像风格,而不是我突然想转变影像风格,然后我才找这样的小说来拍。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创作的内在一致性的。
《撞死了一只羊》
作者:万玛才旦
版本: 广东花城出版社2018年7月
(点击书封可购买)
新京报: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万玛才旦:对。
新京报:可不可以这样说,以《撞死了一只羊》为起点,你的影像会加入一些更虚幻或更魔幻的元素,开始往你的小说靠拢?
万玛才旦:这也不是靠拢。的确,我的小说的讲述方式,还有所营造的意象,跟《撞死了一只羊》是很接近的。在这部电影以前,在我的小说里,只有《塔洛》被改编成了电影。而《塔洛》是一部比较写实的小说。在《塔洛》之前,我的很多小说都不是写实的。所以,以前若大家看过我的小说和电影,就会发现我的小说和电影有着很大的反差。
新京报:你的小说和电影很不一样,但它们有没有什么互相影响的地方?你现在还写小说吗?
万玛才旦:我现在还写小说,但写得不是那么多了。我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学电影。我现在回头看我2000年以前的小说,发现很多其实是可以改编成电影的。
当然,我学习电影也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比如说,我小说里的对话方式,叙事节奏和一些设计都在我上电影学院之后发生了改变。
新京报:你曾说你受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很深的影响,你能谈一下这些影响具体都体现在什么地方?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形式上?
万玛才旦:都有。因为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阅读年代。那时我接触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我一开始接触了很多现实主义的东西,比如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形式比较单一。
在八十年代初期,很多西方现代文学进来了,许多中国大陆的作家也写出了类似的、比较有实验性质的作品。比如余华、阎连科、格非、苏童、残雪等,这些作家都是那时先锋作家的代表。我先有了这样的阅读经验,然后才慢慢进入到写作的实践中去。我也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像《撞死了一只羊》就是带点荒诞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说,这肯定不是我突然转变。
2
打破复仇传统
新京报:你其他的访谈里曾说过,《撞死了一只羊》更关注藏区人民生命个体的觉醒,而不是对于一个族群宽泛的了解。请问该如何理解这种“觉醒”呢?
万玛才旦:我觉得这跟传统有关。在《撞死了一只羊》里面,电影涉及一个复仇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康巴藏区是很牢固的。若有人杀了你的父亲,你就要找到仇人报仇。这个仇人的后代长大以后,就要杀你报仇。这是一个轮回的传统,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的传统,我希望这样的一个传统能够终止。而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这种传统的终止。杀手金巴找到了杀他父亲的仇人,但他最终放下杀他的念头。但是,杀手金巴很难从这样的传统中走出来,因为这样的传统影响力还是很大。对杀手金巴来说,不杀仇人是一种耻辱。
因此,我们就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另一个金巴,他就是司机金巴。他代替杀手金巴在梦中完成了复仇。只有终止了这样的坏传统,个体才有可能觉醒。所以,我们在影片中也会设置一些暗示。在影片的最后,司机金巴在梦里杀了玛扎之后,他走到天葬台。他在第一次抬头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只秃鹫,这是传统的符号。当他再次抬头看的时候,他看到一架飞机,这是现代的符号。到最后,司机金巴好像完全释然了,观众能第一次看到他摘下墨镜的脸,他也露出了很自然的微笑。这些道具和表情的设计,都在为影片的走向而服务。
新京报:在现代化进程中,藏区的变化很大,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很多传统也失落了。这种回不去的故乡、失落、遗憾的情绪,现代化的精神困境在你之前的电影序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塔洛》,这里面冲突是越来越剧烈。像你刚刚所说的,不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撞死了一只羊》里,在梦境里的金巴似乎在现代和传统的对立项中达成了某种和解。这是你对这个问题达成了某种和解吗?你怎么看待这种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统逐渐失落的精神困境?
万玛才旦:我觉得这很难说是一种和解。不是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的。每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都会面对很多新问题,就像《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它们对应着不同的年代藏区所面对的问题。
《撞死了一只羊》的年代设定比较模糊,它可能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或末期的故事,这可能比《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和《塔洛》所设定的年代更早。所以,在电影中,你可能会看到那个年代的一些符号,但是具体的时代所指并不明确。在这部电影中,金巴结束了那样的一个旧传统,走进了新时代,但这并不代表新时代里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到了《静静的嘛呢石》所刻画的九十年代末,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现代的新东西,不断地闯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个年代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新京报:被金巴放下的传统有什么具体的或更深的所指吗?
万玛才旦:在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复仇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一个轮回。所以,这部电影也是用轮回的结构来呈现。司机金巴第一次撞到羊,到最后换轮胎,进入梦境,其实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佛教里面讲,生命是轮回。复仇也是一种轮回,金巴希望去打破这种相对血腥暴力的轮回。
3
寓言体作品
增加文本开放性和审美可能性
新京报:你很喜欢用一些对比或者镜像或者倒影的手法,比如《寻找智美更登》中老板的爱情和蒙面女孩的爱情互为镜像。在《撞死了一只羊》里,两个金巴也是某种镜像或者倒影,一体两面,甚至在倒影里的司机金巴,进入了杀手金巴的梦境。你为什么喜欢用这种手法?不知道这是受到谁的启发?
万玛才旦:没有受到谁的启发。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直接的又有效的表达手法。在我的小说里,我也会经常用到这种手法。这次在《撞死了一只羊》里用得比较多。
两个金巴本身就是一种对比。其中一种是外在的对比——司机金巴看起来很强悍,而杀手金巴看起来很瘦弱;另一种是内在的对比——司机金巴看起来虽强壮,但内心很柔弱,充满着慈悲,他撞了死了一只羊,要把它送到寺院找僧人念经超度。而杀手金巴则相反,他有着找杀父仇人的执念。这个执念引导着他行走了十几年。故事发展到最后,有着如此强烈执念的一个杀手,在他的杀父仇人已经老去时,反而变得很柔弱,心里充满慈悲,大哭一场就离去了。司机金巴在他的梦里反而变得很暴力,替杀手金巴杀死了玛扎。这也一种对比。
《寻找智美更登》剧照
新京报:为什么要用《我的太阳》当作时空转换的一个中介?
万玛才旦:这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很多年以前,我是在高原上听到这首歌的。因为我们之前听的都是帕瓦罗蒂很激昂的男高音。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下,突然听到一首藏语的《我的太阳》,给我一种很荒诞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这首歌,和有关这首歌的记忆。我觉得把这首歌放在电影里很合适。这部电影的讲述方式,本身就不是“正常”的,放这一首歌进去,更能凸显电影的荒诞感。
另一方面,我不会把这首歌很生硬地直接放进剧情中。我也让这首歌跟剧情有一些关联。司机金巴的女儿和这首歌有一个对应关系。在司机金巴和杀手金巴聊天的过程中,司机金巴说,他的女儿就像“他的太阳”一样,这也是他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那时车上挂着他女儿的照片。
在影片结尾的梦境里,奏响的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也许平时我们不会讲某种外语,但是在梦中,我们可能能够听懂某种外语。我用这个来强化梦的荒诞性、不合理性或超现实性。
新京报:你的电影里总有许多寓言或隐喻,就像一个庞大的“隐喻迷宫”一样。你曾在其他访谈中也说过,《撞死了一只羊》的寓言性质很强,你是怎么看待寓言和隐喻对于电影的重要性的?你为何会喜欢用寓言?
万玛才旦:寓言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以前很多人会评论我的小说是寓言体小说。我觉得寓言体的作品会更好。这样的作品虽会有一些模糊性,但它能增加文本的开放性和审美的可能性,也能使一个文本拥有更多的解读维度。特别现实主义的作品让大家想象的空间就比较小。所以,为了让作品的外延增大,创作者要做很多设计。
新京报:所以你ch在创作时,是先想好了要表达的象征意义之后再去设计符号的吗?
万玛才旦:在一些主题或者意义比较明确的作品中会这样。另一些时候,我在创作时是比较模糊的。

4
我们能看到现在导演
拍涉藏题材电影的真诚态度
新京报:在你以前的访谈中,你经常被问到你怎么看待自己藏族导演的身份,你表示不想去区分民族,只想拍出“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但是,你的电影从创作团队到题材和内容,包括你喜爱表现的追寻的主题、失落的情绪、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的故事,它的基底都深深根植于藏文化。但另一方面,你又追求一种普世的艺术表达。你怎么看待这一种矛盾?
万玛才旦: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得面对我选择的题材的问题。我选择了一种题材,就必须得很了解它,以及它背后的文化,这也是我选择与这些主创人员合作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以前很多涉藏题材的电影或文学作品,经常带着某种偏见或者外在的眼光来看待藏族。
另一方面,不管一个创作者面对的是什么题材,首先都要解决创作本身的问题。《撞死了一只羊》虽然是一个涉藏题材作品,但是在创作的层面上,它跟全世界其他创作者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没有区别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一个导演的文化身份跟他作品的关系?比如我们说到贾樟柯会想到他的汾阳。你对这种文化身份会有使命感吗?
万玛才旦:使命感是有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都会对许多涉藏题材的作品感到不满意,因为它们所反映的藏区生活或其他层面的东西很浅,也不太真实。因此,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懂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人,能了解自己民族在当下的处境和现状去创作。这当然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我更希望我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去介入我所要面对的题材。
新京报:那藏族导演这个标签会不会困扰你?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你的藏族身份才关注你?
万玛才旦:这个倒没有。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张扬这样的导演所呈现的藏区呢?张扬的文艺片《冈仁波齐》在内地电影市场受到热捧,票房破亿,类似的题材还有松太加的《阿拉姜色》,这部电影的口碑很好,但相比之下票房表现并不太好,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万玛才旦: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在以前,他们更多地会用一种外来者的目光进行审视。但现在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藏族创作者冒出来了,他们的视角是内在的。他们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比如说朝圣,《冈仁波齐》和《阿拉姜色》虽然看起来是一样的朝圣题材,但它们关注点、着重点很不一样。
而且,这几年创作者们对涉藏题材的态度,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更愿意去用一个真诚的态度对待涉藏题材,更愿意去亲近藏文化、去了解它,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审视,或者有着其他意图的创作。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这种真诚。
《冈仁波齐》剧照
5
“藏地新浪潮”将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
新京报:你也做了松太加的《河》、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的制片人,这两部电影都用孩子的视角展现藏区的人情地缘,跟《静静的嘛呢石》很像。这种表达方式跟许多经典的伊朗电影很接近。你之前也说过,你在电影学院期间很欣赏阿巴斯,还有其他的伊朗电影。所以到底是你建议让他们采取这种视角拍电影,还是说是藏区导演在电影生涯的开端时,会不约而同地在伊朗电影中吸取养分?这是为什么呢?
万玛才旦:这不是我建议他们选的题材,是他们自己选的。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从伊朗电影中吸取养分,也跟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我当年受伊朗电影启发,也同样是这些原因。我之前也想写一些涉藏题材的剧本,但是别人告诉我,这些题材的可操作性不强。我也慢慢地了解到,什么样的题材可以拍,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比较容易地切入现实。这跟外在的因素有关。
新京报:你也曾说过现在的藏语电影仍然处于小众状态。现在像松太加、拉华加等藏族导演也冒出来,你怎么看待“藏地新浪潮”的未来?你对藏语电影有什么期待?
万玛才旦:我觉得在创作的层面上肯定会越来越好。大家对电影的理解也会越来越不一样,人才的储备也会越来越多。创作新人们的追求,对电影的审美和对风格的追求肯定也不尽相同。从形式到内容,未来肯定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丰富的局面。
另一方面,藏语电影肯定也面临着许多困境。首先是市场,中国电影市场还是以汉语为主,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生存难度比较大。当然,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的市场也在扩大,肯定也会越来越好。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6
电影是一种容易让创作者浮躁的东西
新京报:在藏区,你的电影的影响力如何?普通的藏族观众是怎么看待你的电影的?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的电影太“艺术”?
万玛才旦:在2001年《静静的嘛呢石》出现的时候,我在藏区掀起了电影热,许多年轻人也希望来学习电影。现在,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至于会不会太“艺术”,这得分不同的观众。
新京报:想知道你的下一部电影《永恒的一天》现在进展如何?这部电影跟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和一日》有什么关系吗?
万玛才旦:剧本已经完成了,现在在等待时机。跟安哲罗普洛斯那部电影没有什么关系。
新京报:你对现在的青年导演有什么寄语吗?
万玛才旦:电影可能是一种容易让创作者比较浮躁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们不要浮躁,希望他们能好好地去解决创作本身的问题。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采写:徐悦东;编辑:榕小崧;校对:薛京宁。题图素材来自《杀死了一只羊》(2019)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过春天》:没有堕胎和狗血,依然拍出了硬核青春
十年漫威:票房爆炸的“复联3”将断送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