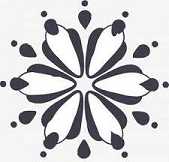奉读慈谕,忆昔恩泽
发布时间:2022-11-28 08:18:55作者:楞伽经讲什么奉读慈谕,忆昔恩泽
释昭慧
导师圆寂后三天,六月七日,《慈济》月刊要我写一篇追思文章。当时心里不免迟疑——忙碌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原因是:痛失恩师的心情,尚未完全调适过来,哀思深切,反而无言。一旦承诺,怕会辜负所托。
六月十九日晚间,取出了珍存已久的宝藏——那是二十二年前初识导师,与导师之间的几封往覆信札。忽然想到,既然无法表述当前哀思,何妨将尘封在岁月底层的记忆掏取出来,与读者分享初识导师时的喜悦心情呢?
我给恩师的第一封信,签押的日期是“七二、二、十八”,信里还只是称他为“老法师”。信中说道:
“元月十六日与致中法师及三位居士驱车拜访,得以亲聆 法音,一偿宿愿。对 您老的慈蔼颜容及殷切教诲中的悲智流露,留下深刻的回忆。”
这封信提示了一个我生命中的重要日期——与导师在台中华雨精舍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十六日。那年,导师七十八岁,我二十六岁,距离我出家之期,已有四年半了。
原来,出家之后的我,对现况有着说不尽的失望之情;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规制方面,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总是让我隐约嗅到一些反人性的因子,而深感不安与不妥。我不知道正确的佛家思想与规制究竟是什么?应当作何诠释?我因身心无法安顿而深深受苦。
七十一年底,我离开了剃度常住,也开始研读导师的著作。读着读着,许多长久无解的困惑,竟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差堪比拟我那时的无限法喜!我曾以叔本华对《奥义书》的赞语,拿来赞叹导师的著作:“它是我生前的安慰,也是我死后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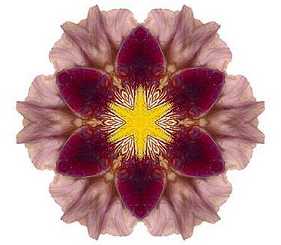
五页请益,十二页覆函
手边第二份与导师之间的往覆信函,是在收到导师首封覆函后一个月写的。
七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我夹问夹议写了一封五页信函,谈的是有关他在《佛法概论》中所提到“淫欲不是生死根本”的问题。那封信现在看来,还真有点啼笑皆非,因为我竟然在第一段写道:
“弟子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明明知道您多病、忙碌,偏是又去信、又往访的,干扰您的生活。但自入佛门以来,再没有比读您的著作更喜乐的事了!长期接受这无声的恳切教诲,使您在弟子心目中,无疑是永远的舟航。明师难遇,在学道过程中的疑惑,若不把握时机切问近思,以后将会造成怎样的遗憾啊!因此,请 原谅弟子再‘不懂事\’一次,慈悲启迪弟子的愚蒙!”
摆明了自己就是要“不懂事”地缠着他问问题。是这分“跟定了善知识”的愚诚打动了他的心,还是自己提出的问题,让他觉得很有答覆的价值?不得而知。总之,这封共计五页的请益函,竟然换得了一封长达十二页的导师亲笔挂号覆函。而我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介籍籍无名的小尼师而已。
在覆函之中,他详细而完整地,向我解释了有关“淫欲与生死根本”的法义。信函中所押的日期,则是“四月廿六日”。十年之后,民国八十二年四月,导师八十八岁,将尚未集结出版或发表的作品,编辑成五册《华雨集》出版;该封长函,就编到《华雨集》第五册中,题为“答昭慧尼”。
不合时宜?时不合师宜!
我的第五封呈导师函,信末押的日期是“七二、十二、廿四”,也就是认识他的第一年年底,那时我已住进高雄市兴隆净寺。
记忆中,在写那封信之前不久,我到台中华雨精舍,言谈之中,导师轻喟他实在“不合时宜”。我感受到他的孤峰独拔,先知寂寞,但不知要如何接腔,只能默然以对。
回到寺里,好似要给老人“打气”一般,我竟然不自量力地写了如下的一封信函:
“听到? 您自叹‘不合时宜\’,弟子也不免感慨系之,直下觉得:应说是时不合? 师宜,非是? 师不合时宜。‘古来圣贤皆寂寞\’,孔子何尝不兴‘乘桴浮于海\’之叹?释尊成道之刻,不也对转*轮的大业,颇费一番踌躇吗?先知的寂寞,未必在于缺乏拥戴者,而是往往拥戴者与反对者同样罕能体会(尤其是体现)他们所宣教的真理。‘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这大概就是世间的常态吧!”
“您把毕生的心血耗注在经论的研究整理上,解决了许多教证上的疑难,也铺设了后来者便于深入教法的康庄大道;弟子何幸,晚导师半世纪生,得以沐浴膏泽。面对这些体大思精、一部又一部的论著,真希望能在此后的岁月里,一面撷取您已栽成的丰硕果实,一面赓续您所未完成的志业。虽然事关智慧才情,但那怕是在您已踏出的百千步之外,再踵继一小步,总也算是对您、对三宝、对众生的一分小小的报答吧——您看到这里,大概要笑弟子是‘初生之犊\’了。”
读到“初生之犊”这么一封几乎是以“薪火相传”毛遂自荐的来函,内敛的老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是在莞尔之中,带着些许欣慰之情吧!
悲智庄严,永远的青年
在这之前半年,七十二年四月间,读完导师《青年的佛教》一书,内心深有所感,写了一篇题为“永远的青年——印顺法师《青年的佛教》读后感”,盛赞导师“将被世人称颂为永远的、悲智庄严的青年!”
五月四日,我将该份文稿补寄给他,并呈第三封函云:
“慈诲恭悉,敬谨受教。既沐浴以法化,深恩不言谢。乃呈近日习作《青年的佛教》读后感”乙篇,聊表孺子景慕之忱。所愿不至流为庸俗之歌功颂德耳!”
导师在香港的大弟子慧莹长老尼,在《菩提树月刊》读到了“永远的青年”,七十三年初返台之时,问到导师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他竟向老徒弟说:“这是我的小知音!”
没想到就因导师这句话,让慧莹长老尼带领信众仆仆风尘,南下高雄寻访,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一天,慧莹法师突然来到,看到甫自大寮(厨房)赶来,连围裙都来不及解开的我,第一句就是:
“我特别来看导师的小知音!”
这句话对我的鼓舞,非比寻常!试想:如果我听到的是她转述导师说:“那小子文章不值一读!”我还有勇气写下去,而且一写二十多个年头吗?
在那之后不久,我去拜望导师,他忽然问起我的生活情形,闻后静默不语。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谈到自己的“生活”。
在此之前,我拜望他,一向只询问法义。虽然我也知道,他若知悉我忙碌的生活情况,可能会帮我改善,但我从不曾向他谈到自己的处境。原因是,在我的道德意识中,一向不允许自己将别人当作达成目的的工具,更何况导师还是我心目中崇仰的大德!对一位大德的景仰,必须是全然纯净的“法之向往”,而不宜夹杂一丁点儿图己的私心。
过不了多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亲笔函,信中写道:
“你从阅藏而到现在住处,从一位可以向学,愿意向学的人来说,似乎不是很理想的。新竹福严佛学院,继续办理(初级)招生。我想你如愿意到新竹,住在学院,每周先授几点钟国文,其他时间,可以自己修学佛法。环境也许不完全符合你意思(完全满意是难得的),但至少有充分的时间,对佛法作进一步的深入。你如有意的话,我当代向学院负责人介绍,再由负责人进行洽聘。希望你接信后考虑一下,就给我回信。我想你的信息,会使我欢喜!”
信末署名并押日期“五、廿一”,这已是认识他的第二年了。他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高不可仰,但这封手谕的字里行间,却又是这样的谦和温厚,含蓄地表达着长者对后生晚辈的深切关怀。
我捧着信函一读再读,感觉自己简直像是童话故事中,衣衫褴褛而骤得金缕鞋的灰姑娘!
就这样,在导师的提携之下,我与福严精舍结下了不解之缘。贵人相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慈荫后学,恩深义重
七十三年九月,我背着行囊,承载着导师的关切与祝福,到了新竹市明湖路观音坪上的福严佛学院教书。这一跨步,就是三年山居清修生活的开始,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捩点。
直到很久以后,偶尔在导师座下其他弟子的转述中,我才知道自己来到福严精舍的因缘:当日慧莹法师南下寻访我之后,回到华雨精舍,基于护念与不舍,而向导师报告了我的忙碌情形。难怪导师会在其后垂询我的生活状况。
导师是一位相当内敛的人,待我报告之后,他当场静默不言,但想来那时他心中已有定见。不久后,正在筹备第四届招生事宜的福严佛学院副院长依道法师与训导主任慧润法师去拜望导师,他垂询国文老师的人选,并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位!”话就到此为止。
可能就是这样,不久后,他写了那封被我珍藏至今的亲笔函,然后才在我立刻雀跃覆函之后,下一次与慧润法师他们见面时,点名介绍了我。
一直到民国九十年,江灿腾教授出版新书《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家——以印顺导师为中心的薪火相传研究论文集》,附录导师给他的一封亲笔函,我从该一信函之中方才得知:自己竟然是他生平唯一亲自推介到佛学院教书的人。
还有一次,慧润法师在闲谈之中告知:“导师特别交代我们:不要把行政工作分摊给你,好让你除了教书之外,得以全心做学问。”
知道了自己来到学院的背景,以及导师对自己的期许之后,我格外感念到师恩深重,所以在这样一个静谧的环境里,除了准备国文教材、批改学生作文之外,其他所有时间都专心研读教典,并尽量拒绝各方邀约演讲之类的外缘。
也幸好在导师的指导之下,有系统地研阅三藏,扎下了厚实的学术基础,这使我得以展开佛学专业论文写作的生涯,迄今共写了二十三部书,还有许多论文与时论,无暇整理付梓。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那三年的沉潜修学,是不可能产生尔后这些学术成果的。
常言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民国七十七年初,我跨出了清幽的山门,投入了滚滚浊流的尘寰之中,自此就是一条生命的不归之路。
我相信那时导师会隐约担忧我学术生命的夭折,也会担忧我禁不起世间的诱惑而变质。但是差堪告慰的,我的学术生命不但没有夭折,反而在研究议题方面,更有了“柳暗花明”的广阔视野;我不但没有在名利场中面目全非,反而在诸多的人事历练之中,心思更为纯净而豁达,任事也更为勇猛而俐落了。
有了三年山居岁月的学养基础,其后的忙碌生涯,就好似提供了各种层面的实践机会,好让我以实务经验来一一印证理论,又依此而拓展视界,将佛法拿来与当代对话。于是佛法不但没有离我远去,反而更深刻地铭印在我的心中。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导师慈悲的引荐与智慧的指引,让我有三年在福严精舍山居研教的基础,我能在人生涧道无数个峰回路转之后,依然保持一潭湛然澄清的“出山泉水”吗?
是故对印公恩师、对福严精舍,以及这段生命岁月中所会遇的师友们,我至今仍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恩之情;而这分心情,或许就是让我誓愿尽形寿孜孜矻矻以护持正法、利济有情的最大动源吧!
——转载自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463期《慈济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