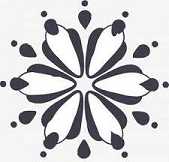法尊法师: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
发布时间:2024-06-12 03:29:13作者:楞伽经讲什么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示寂于上海,噩耗传来,悲痛欲绝;茫茫苦海,骤失慈航,昏昏长夜,谁为宝炬?推心泣血者岂仅余一人而已哉!况余亲灭,慈颜二十余载,若学若行无一不秉大师之慈旨而为之,而今而后将何所凭依,又何怪乎闻讯之下,手足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宛如泥塑乎?呜呼痛哉!
亲近大师之回忆
回忆民国十秋,初谒慈颜于北平广济寺,即蒙慈悲摄受谆谆教诫,谓将于武昌办佛学院,勉令入院修学。

毕业后,复奉慈命赴北平,参加藏文学院,追随勇师,进学西藏佛法,期将来互译汉藏典籍,以沟通汉藏之佛教及文化。十四年春,国民革命军将兴师北伐,大师旋命勇师率全体学生提前进藏。此后数年虽未能常侍巾瓶,然屡承赐函指教,固仍在慈悲护念之中也。
民十九,大师入川朝峨山时,曾发表世界佛学苑之计划,赐函甘孜,命余回国主持汉藏佛学系。斯时余对西藏佛学甫获门径,尚未深造,不欲中道而止,故覆函辞谢,并愿介绍西藏大德安东格什至内地弘法以自代。
二十年春,余进昌都拜见安东格什时,详陈大师组织世苑之计划,及拟迎请安东格什至内地弘法之意。深蒙安东格什嘉许。但因赴藏之计划已定,不便即时来川,只可俟到藏后,再筹划前来。安东格什于是年冬抵拉萨后,示疾甚久。二十一年秋,世苑汉藏教理院正式成立,大师又函电交驰,促令迎安东格什入川主持。(但西藏佛教之组织与内地不同,凡有学德之高僧【无名僧众不在此例】有所行动,须先请示达赖,得其允许方可成行。故为迎请安东格什一事,余亦曾数数呈请达赖,并请人善为说辞。直至达赖圆寂前,仅批准余先返内地筹备)。但以因缘未熟,事卒无成。
二十三年夏,余始返抵上海,端午前往宁波拜见慈颜,当奉面谕,入川办理汉院。此后每值寒暑假期,辄赴武汉等处,晋谒慈颜,报告院务,并请示进行之方针。二十六年抗战军兴,余即迎请大师莅川,常住汉院。所有院中一切措施,皆由大师亲自主持。虽有时弘化蓉渝黔滇湘等处,然总以汉院为基本道场。故此数年中所受慈诲,较昔在武院所受尤多。胜利后大师东下,院事交余负责,自知绠短汲深,时多陨越。正思每值寒暑假请示一如往昔,何意大师遽弃余等不肖弟子而上生都史多也。呜呼痛哉!
大师之救教运动
余前后亲近大师二十余年,对于大师之悲愿与事业,多所闻知。总觉其一切措施,胥由复兴中国佛教之伟大悲愿所激发,实无一毫名利等念羼杂其间。故事业之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大师于幼年,即值清庭变法维新,目睹各处教育当局,往往借经费无出为名,驱逐僧众,占据寺址,提拔僧产。此汹涌之洪流,到处泛滥,几有漂没整个中国佛教之趋势。又见一般护法居士,大声疾呼,劝僧众自觉,劝士大夫等勿任性妄为,复因华山法师示以新学诸书而加以鼓励。大师遂暂置阅藏参禅等静默之修行,出而从事复兴中国佛教运动,参加僧教育会等,是为大师伟大之悲愿及其事业之发端。
次觉各处之僧教育会,组织多未臻完善,致弊端百出,又值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政府成立,大师乃从事组织一完整之佛教团体名曰佛教协进会;期实行其改进佛教之计划,俾隐没多年之佛教教理重放光明;而于停滞之教制,私有之教产,皆加以革新;俾流行千百年之古佛教,适合于现代之中国社会,而成为自行化他之新佛教。果能如是,则非但教产得以保全,且能化民成俗,发挥佛教六度四摄之大用,岂不善哉!大师由伟大之悲愿而推动其佛教改革事业之初步也。
整理僧伽制度
民国三年后,大师掩关于普陀山、对于性相台贤各家之教理,及中外古今诸家之学说,俱作精密而有统绪之研究。著述有《楞严摄论》等,并于周易及荀子墨子等之学说有所阐明。复撰破神执,订天演等文,以破世间之执着。其尤要者,则为复兴中国佛教之张本,根据戒律,衡量时事,而造成之《整理僧伽制度论》也。
盖大师以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二千年,历史演变,时有盛衰隆替,自隋唐全盛之后,宋元以降,渐就凌夷,迨有清末叶,衰颓遂达其极。苟无大心菩萨出而振兴之,长此以往,惟有出于灭亡之一途而已,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已一跃而为共和立宪之国家,则中国佛教之僧制,亦应依据佛制加以修改,使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所需要之佛教僧制也。此整理僧伽制度论,虽不为一般顽固之寺院所欢迎,甚至为一般狮子虫所反对。但此实救治中国僧制之灵方,亦即大师广大悲愿之结晶也。
民国六年,大师出关后,往台湾弘法,并远赴日本考察其佛教组织,愈证明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切要,返沪后,即组织觉社,广事宣传。次为实行此种制度起见,及接管杭州净慈寺,深思以此寺为基础,而推行其改革僧制之计划。不意当时腐恶之势力太强,嫉异憎恨,多方阻挠。大师自觉为此一寺耗如是精神力量,未免事倍功半益少损多,乃放弃净慈,专行教化。
此次推行改革僧制虽未成功,然对于日后之创办武昌佛学院等,实为一有力之动源。
创办僧教育机关
大师以改革僧制,如仅就旧寺使起,必经多次风波,且未必能收成效,所需用之人才,复甚缺乏,必须先办教育机构,训练干部人才,以后推行或可较易。以是于讲经武昌时,与武汉热心护法之居士等,谈及改进佛教,须养成基本干部人才。当时得李开侁居士等之热烈赞助;复觉借用寺庙障难易生,决定自购地基,新创学院,如是遂有武昌佛学院之产生。其中课程虽多采用日本佛教大学之方式,管理制度则参用丛林规约,而朝暮所诵持者《弥勒上生经》等,内心所依止者,瑜伽菩萨戒本也。故大师尝云“吾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亦即武院此时之口号也。
此学院所产生之人材,现多为各处办理学院之法师。以是武院之学风,影响于全国佛教徒众者甚大,迄今凡办理僧教育之寺院,颇多以佛学院名之,故此十余年来,中国佛教稍露转机者,大师之悲愿所造也。
从事世界佛教运动
世界佛教运动,即是推行佛法于全世界,以阐明真理救济人群之运动。此为大师毕生一贯之大悲救世精神。初于民国十二年夏季,建设庐山大林寺讲堂,邀集各界热心佛法之人士,讲演佛学,当时来听讲者,颇多信仰基督教之中外人士,并时有外国牧师参加,由此遂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从事国际佛教运动之思想。为欲使各国人士信受佛法,于是创祖“世界佛教联合会”。至十三年夏,不特有日本代表参加,即德美及芬兰等国之佛学家亦多特来申请加入。
大师复以当时世界各国及其人民,无论其做人或立国,皆以本国或自我之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损失他人或他国。故其结果,终必走入战争一途,毁灭自他而后已。如能将大乘佛教利他之思想传布世界各国,或可使其做人立国之思想有以根本改善。
盖宇宙万有,悉从众缘所成,绝无孤立独存之个体,欲获得个人之利益。必须先从众人利益做起,苟大众俱能获益相安,则个人之利益,实亦自然而得。是则不仅人与人之间,应相资相成,即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亦必须相助相益,以求共存共荣,不应有损人利己杀人活己之暴行也。倘以此种佛教之真理感化世界人心而获成功,则世界之纠纷自然而解,永久和平不难实现,而中国亦可跻安,即整个世界乐矣。
大师依上述之意义,不辞劳瘁,远赴欧美,一方面考察各国之政治、经济、宗教等,一方面应各界之邀请,宣讲佛学,感化人心。在法国巴黎时,发起组织“世界佛学苑”,遍于英德意等国设通讯处,尤以法国朝野人士热心赞助者颇多。此举虽终以经济困难,未克圆满实现,然尔后之改武院为世苑图书馆,及创设汉藏教院,皆世苑直属事业之一斑也。但以时值末法,人心险恶,世界变乱,虽有明师良药,其如不信不受者何。然大师感化世界之目的虽未达,而其悲愿之宏深,终为万世所景仰。
组织学会教会
中国佛教,如前所述,代有盛衰隆替,满清以后,制度分歧,各处寺院,不相连系,若盛若衰,胥视其得人与否而已。迨遘满清之变法维新,为提产兴学之风潮所打击,几全体覆灭,无法自存。故诸高瞻远瞩具大悲心之大德,急起高呼,组织教会,以挽救此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大师初期参加各处之僧教育会,又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后复合并为中国佛教总会,亦皆适应当时之需要者也。
民国六年后,大师本挽救佛教之大悲心,为整理僧制之准备,于是有中华佛教联合会之组织。十五年后又为适应时局之变化,著僧制新论,复为补救新僧之流币,作《革命僧之训辞》,其受业诸生,则组织“现代僧伽社”等,宣传、鼓吹、推行改革僧制之计划,以求衰颓之中国佛教渐获转机。讵意一般狮虫,非但不能觉悟、奋兴、响应、推行,反以其不利于己之藏垢纳污,从而诋訾、掊击,尽力阻挠之。此诚令人长太息者也。
民国十七年后,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有将寺产没收,以举办社会公益之趋势,各处寺院,为此风涛所震骇,始感觉有共谋团结力图挽救之必要。大师适于斯时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于是麋集于此伟大旗帜下,对于大师之筹措教会经费,办理僧众训练,以及推行复兴佛教之事业等,多表赞同。
但经多方设法,寺产获得相当保障之后,则一般僧寺,又恢复其苟且偷安之状态,对于佛教会之事业,付诸不闻不问矣。如是一般僧寺,事急则闪电交驰,事息则因循苟且。任组织何种教会,终无实际改善之希望,即如抗战期中,大师驻川数年,凡遇外界有不利于佛教之动向,必先事设法,预为防范,以及计划寺院应如何改进等。凡此种种,非特不能得多数僧寺之同情,反多误会为破坏佛教者。甚至于开会时,公开攻击毁谤之。是以大师驻川虽久,而其主张,能见诸实现者,实属寥寥无几。
余尝白大师曰:寺院既多如此腐败,僧众又多如彼冥顽,纵教会组织成功,亦必无使其改善之希望。况欲改善僧寺,须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无能改善之人才,则何从使僧寺改善。例如现在各地,一般虚有其名之佛教会,其中办事之人,多系必须淘汰或改善之对象。以此等人办理会务,安能望其会务办好耶。
大师则曰:因为不好办,所以要发心去办,只要有一长可用,即须用之。倘使教会合法成立,渐次训练人材,渐次加以改进,非绝对不能办好。且有教会成立,则对外侮有以御之。保护教所,亦属菩萨应行之一事也。
由斯以言,可见大师发心组织佛教会,纯为菩萨悲愿之所激。虽对佛教会并不怀过分之奢望,但为保护教产,仍不惜精神劳力而为之。而其为之也,又早知其不可为。此其大悲愿力,尤不可及也。
筹办菩萨学处
大师改进佛教之计划,初期原以中国佛教为对象,思将中国大乘佛法弘扬推行于全世界。次见中国佛教整理甚难,乃转而欲先从国际着手。后以世界战祸连结,弘化欧美,亦非短期所能奏效,迨出国访问印、缅、锡兰等处佛教之后,改进佛教之思想,又稍有转移,仍觉欲真正改进中国佛教,必须先建立一所模范道场,训练一般中坚干部人才,组织适合今时今地之佛教集团机构,使社会人士改善对佛教之观念,使其他寺院仿效学习,渐次迁善。初即名之为“今菩萨行”
大师尝论云:“中国佛教所说的是大乘理论,但不曾把他实践,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现在行为上。故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行,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锡兰虽是传的小乘教理,而他们都能化民成俗,使人民普学三皈五戒,人天善法,举国奉行,佛教成为人民的宗教,并广作社会、慈善、文化、教育等事业,以利益国家社会,乃至人群,表现佛教慈悲,博济的精神。所以他们所说的虽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大乘行。”
故大师以后转注意于如何实行济世化众之行为,以发扬大乘佛教之真精神,而从事济世利人之实际行动。后又将制度加以调整,改名曰“菩萨学处”。大师在川时,曾派人赴合川,贵州等处试办,俱以人才不足而告停歇。胜利后,又拟于当阳玉泉寺试办,亦未成功。直至圆寂前一个月,犹在宁波延庆寺以菩萨学处之推行,嘱累诸弟子。大师复兴中国佛教之大悲宏愿,实无言辞足以形容之。
总观上述大师一生之职志,若参加僧教育会,以谋挽救教难。若接管净慈寺,以图整理僧制推行。若创办佛学院,训练干部人才,以求进行改进佛教之计划。若从事世界佛教运动,以期挽救全世界之人心,缔造全世界之永久和平。若组织佛教会,以事保护教产,改进僧制,弘扬佛化。若提倡今菩萨行,组织菩萨学处,以祈推行大乘佛教救世之真精神等,无一不从大悲弘愿等流而出,故吾亲近大师二十余年,所见所闻,唯觉其纯属一大悲弘愿之体现,而无一丝一毫名利私意羼杂其间。
继承大师事业之集议
大师示寂之后,若出家若在家众弟子辈,咸集沪上,除照一般仪式荼略大师遗体,收检灵骨舍利,分行建塔供养外,对于如何继承大师之遗业亦尝集议及之,惟以大师所举办改进佛教之事业为数甚多,若祈一一继续进行,实力有所不逮。故当加以检讨,择要而行。
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机关方面,则大师所创办之武汉两院,必须力图其继续进行,以备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为大师二十余年来弘扬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论经费如何支绌,必须设法继续印行,以为推行大师之思想及事业之指针。大师丛书为大师毕生思想学行之结晶,必须速疾编纂完成,以作后学推行复兴佛教运动之范本,此外如佛教医院,大雄中学,觉群周刊,及某某学院等,虽亦大师弘扬大乘佛教济世利人之事业,但或以办理未善,或以主持有人,众弟子辈,如有余力,当力谋发展。苟力有未逮,则听凭旁热心人士办理。至中国佛教会,为全国性之佛教事业,以大师之学养德望,办理犹感困难,若以才能学力俱不充足之后学承办,必更多诸障碍,非惟无益,恐反招致愆尤。故于此事,当听凭全国佛教徒商讨进行。
兹更结以数语曰:凡吾同志苟真欲继承大师之遗业,推行改进佛教之计划者,则必切实表现于作为,方为善继善述。否则空口说白话,或仅以笔墨写成文字,则大师之遗著,详且密矣,更何待后人之徒劳口舌笔墨哉。象王已逝,今后复兴中国佛教之责任,唯在后起有志之僧青年。言而不行徒增绮语,故吾于大师示寂后,实不欲多言,亦实觉更无可言者,谨望有志之僧青年,各自勉旃。
丁亥端阳日
太虚台记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六日,即夏历戊寅年腊月十八日,为尊等亲教太虚大师五秩诞辰。念二十年来,备受甄陶,深思就本院有以纪念之,商之同门法舫圣观之信等,爰议建石台于狮峰,即以大师之德号名之。于是策杖登峰,勘地绘图,斫榛焚茅,鸠工齿石,不期月而台成。登台四顾,游目骋怀,嘉陵之胜,缙云之景,一览无余矣。深觉我大师文章道德,与兹峰兹台同永。绝壑愔愔、幽林蔚蔚、深远茂密,大师之清净相也。松竹清风,郁郁菁菁,冷然成,大师之微妙声也。一花一草,一泉一石,动容悲愿,大师之普贤行也。贞固干教,隐括矫时,剑无其利,镜无其朗,高踞毗卢之顶,握法王之正印,惟大师屹然当之。有时振威一吼,魔外慑伏,圆音才演,四众向化,诚不可得而思议也。夫后之来者,登斯峰必登斯台,高瞻远瞩,旷观千古,当有以知大师之志行而向往之者。告竣之日,勉书数语,用彰胜德云尔。
一九三九年春,法尊谨识于汉藏教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