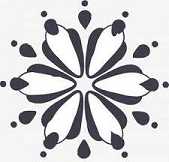巨赞法师: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
发布时间:2024-12-22 03:28:37作者:楞伽经讲什么
禅宗发展至唐末,禅师们在上堂、小参、拈古、勘辨时所用的语句,大都讲究修饰,有时还用对偶很工整的韵文,如唐懿宗咸通年间,有僧问夹山灵泉禅院的善会禅师:“如何是夹山境”?善会答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禅境诗情,极为浓郁,因而传诵一时,夹山也被禅子们称为“碧岩”。其后数十年,法眼文益禅师在《宗门十归论》里说:
“稍睹诸方宗匠,参学上流,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为未事。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语。自谓不拘粗犷,匪择秽孱,拟他出俗之辞,标归第一主义。识者览之嗤笑,愚者信之流传,使名理而寝消,累教门之愈薄。不见《华严》万偈,祖颂千篇,俱烂漫而有文,悉清纯而靡杂,岂同猥俗,兼糅戏谐。在后世以作经,在群口而为实,亦须稽古,乃要合宜。苟或乏于天资,当自甘于木讷,胡必强攀英俊,希慕贤明,呈丑拙以乱风,织弊讹而贻戚,无惑妄诞,以滋后羞。”
一代宗师,这样竭力提倡语句的修饰,自然会影响禅风(宗门的风气),而法眼自己也经常用诗偈说法。如《冷斋夜话》卷一云: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
这段记载如果是实在的话,则法眼不但以诗偈谈禅,而且又以之论政,在这样的场合,语句当然非讲究修饰不可了。
法眼圆寂之后二三十年,汾阳善昭禅师创为颂古,在上堂、小参等方面所用的诗偈就更多。

“颂古自汾阳始,观其颂布毛公案曰:‘侍者初心慕胜缘,辞师拟去学参禅;鸟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获心安。’与胡僧金锡光偈,看他吐露,终是作家,真实宗师,一拈一举,皆从性中流出,殊不以攒华叠锦为贵也。”
其实,在《汾阳无德禅师语录》里,诗歌偈颂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真可以说是“烂漫有文,清纯靡杂”了。
稍后于汾阳的雪窦重显禅师,素以“工翰墨”见称,他在未悟道的时候追慕诗僧禅月贯休,有诗云:“红芍药边方舞蝶,碧梧桐里正啼莺。离亭不折依依柳,况有青山送又迎。”造句清新,意境深密,的是诗中上品。他得法于云门宗的智门光祚禅师之后,意境更高,造句更奇,如他在就任雪窦寺住持的时候,上堂云:“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气韵高卓,似有过于善会禅师的答“夹山境”。
云门宗的开山祖师文偃禅师,气象阔大,机锋迅利。法眼禅师在《宗门十规》里以“函盖截流”四字称颂他。“函盖”就是云门“三句语”中的“函盖乾坤”。缘密禅师(云门的弟子)颂云:“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是就体上说的。“截流”也就是“截断众流”,缘密颂云:“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是就用上说的。体上一切现成,用上纤尘不立。云门说法,雷奔风卷,纵横变化,总不出此范畴,而具体表现在他的“一字禅”上。
可是他的语句,有时不免像法眼所非议的“野谈”或“俗语”,当时有人嫌他“太粗生”。二传至智门光祚禅师则有所改进,如智门颂文殊白椎公案云:“文殊白椎报众知,法王法令合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不待眉间毫相辉。”格律声韵都很工稳。
雪窦久受智门的熏陶,又受了汾阳等人的影响,他的文学天才和宗门悟境就融结为《颂古百则》,成为法眼所说“歌颂制作”的典型。《颂古百则》所引用的公案,除《楞严经》二则、《维摩经》一则、《金刚经》一则外,其余九十六则中,以云门宗的公案为重点,云门文偃禅师一人的公案共有十五则,就是一个证明。至于理境,也像他的其余六种著作一样(雪窦有《洞庭语录》《雪窦开堂录》《瀑泉集》《祖英集》《颂古集》《拈古集》《雪窦后录》七种),发扬了“函盖截流”的主旨。所以《补续高僧传》卷七说:“云门一宗,得雪窦而中兴。”
可是雪窦的《颂古百则》得到临济宗杨歧派圆悟克勤禅师在住持夹山灵泉禅院时,加上评唱,组成《碧岩录》(或称《碧岩集》),而被当时的禅僧们称为“宗门第一书”。
这一事实说明,禅宗从唐末发展至北宋,不但在语句的修饰上达到了空前成熟的程度,而且在宗派之间也倾向于合流。《续传灯录》卷七《杨岐方会禅师传》中云,“其提纲振领,大类云门”。
又,宋高宗绍兴三年耿延禧《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序》云,“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诸佛此一音,六代祖师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昔杨岐以此音鼓簧天下,至圆悟大禅师,此音益震”。
可见,临济宗的圆悟禅师,根据云门宗雪窦禅师的颂古,加以评唱,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续传灯录》卷二十五《克勤禅师传》云:
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法演)。
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提刑应,喏!喏!
祖曰:“且子细。”
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
祖曰:“他认得声。”
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
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
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
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
圆悟从小艳诗悟人,悟后诗偈深得诗中三昧,可见也是一个极有文学天才的人。他引雪窦为同调,评唱《颂古百则》,当然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圆悟在雪窦《颂古百则》的每一则公案和偈颂的前面加上总论式的“垂示”,又在公案和偈颂的每一句下面附以短小精悍的“著语”,然后分别在公案和偈颂的后面,用大段文字拈提宗旨和交代公案的源委,给予参禅的人以很大的方便,所以当时用“丛林学道诠要”、“留示丛林,永垂宗旨”、“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奥”等语赞美它。
禅宗五宗七派的祖师们本来各有机用,不易“凑泊”,自《碧岩录》出而有“敲门砖”可寻,禅风又为之一变,因而引起当时一部分禅师们的愤慨,《禅林宝训》卷下引心闻昙贲禅师之说云:
“天禧间,雪窦以辩博之才,荚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已意,离(厘)之为《碧岩集》,彼时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莫能回其说。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习术坏矣。”
心闻禅师和道宁禅师等虽然不同意《碧岩集》的作法,可是“新进后生”护拥它。据延佑年间径山住持希陵的《碧岩录后序》云:
“大慧禅师(圆悟的弟子)因学人人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自悟。”
这大概就是“新进后生”护拥《碧岩录》的原因,也由此而发生了弊病。又《禅林宝训》卷下云:“今人杜撰四句落韵诗,唤作钓话,一人突出众前,高吟古诗一联,唤作骂阵,俗恶俗恶,可悲可痛。”
这或者可以说是更大的一种流弊了。因此大慧禅师要把《碧岩录》的刻版毁掉,企图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不过,大慧禅师并没有能够杜绝这种“禅病”,因为毁版之后不久,就重行刻版,而且在重刻的《序》《跋》上有这样说法:
“圆悟顾予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立语虽似调和,而用意则为《碧岩录》张目。”
说明《碧岩录》的影响并未因大慧毁版而有所动摇。为什么?我以为应该研究一下心闻禅师所说的“笼络当世学者”一语。禅宗的集大成者惠能禅师(即六祖)本来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出世之后,为了直指心性,语句都很质朴平实,后来的禅师们如青原、南岳、马祖、石头、百丈、药山等等,都亲自开山种地,参加劳动,所用语句也大都开门见山,质直无华,所以只要机缘凑合,村姑野老也可因而悟道。如马祖位下的凌行婆和以后的台山婆、烧庵婆等,见地透彻,机锋灵活,并不让得道的高僧。可见当时的禅风,比较接近于人民大众。
后来禅宗的影响不断扩大,士大夫们逐渐被吸引到禅宗方面来。冠盖莅临禅门的次数愈多,村姑野老们自在参禅的机会就愈少,到了北宋,禅宗门下,除了禅和子以外,就只见士大夫们憧憧往来,很少有村姑野老们的足迹。翻开《雪窦禅师语录》,就可以见到雪窦禅师和曾公会学士的交谊之深,和驸马都尉李文和、于秘丞、沈祠部等也常有往还,他的荣任雪窦寺住持,就是出于曾公会的推举。
圆悟禅师和士大夫们的来往更密,他经常为运判、侍御、待制、朝散、安抚、少保、典御以及贵妃、郓国大王、莘王、济王等达官贵人上堂说法;历任名刹的住持,也都出于士大夫们的推举。
士大夫们鄙视劳动,爱好“斯文”,所以禅师们就不得不抛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锄头,拈起吟诗作赋的生花之笔来了,所谓“笼络当世学者”似乎可以从这里去体会。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禅宗史上的这一个发展,而是说明,自唐末至北宋,由于禅师们逐渐脱离人民大众以笼络士大夫们,禅风由质朴而变为讲究修饰语句,影响所及,极为深远,愈到后来就愈甚。
这里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个例子是:著名的禅师舞文弄墨,一般禅和子们也依样画葫芦。
如雪窦禅师在杭州灵隐寺上堂说法,有僧问:“宝座先登于此日,请师一句震雷音!”师云:“徒劳侧耳。”(僧)进云:“恁么,则一音普遍于沙界,大众无不尽咸闻。”
圆悟禅师在成都万寿禅寺上堂说法,有僧问:“宝剑出匣,海蚌初开,向上宗乘,乞师直指。”师云:“横按莫耶全正令。”进云:“恁么,则坐断十方去也。”师云:“七纵八横。”进云:“宝藏拨开于此日,五叶千灯事转新。”
宾主问答,都在造句用语上费了推敲,是否可以说是“老实商量”,我以为是有问题的。大慧禅师虽然毁了《碧岩集》的版子,可是在他的语录里,宾主问答,也是如此。如他在临安明庆院开堂说法,
僧问:“人天普集,选佛场开,祖令当机,如何举唱?”师云:“钝鸟逆风飞。”进云:“遍界且无寻觅处,分明一点座中圆。”师云:“人间无水不朝东。”进云:“可谓三春果满菩提树,一夜华开世界香。”
这说明风气已成,无法改变,明知流弊甚多,也不能不随波逐流。其实大慧禅师提唱“参话头禅”,也无非是以“敲门砖”给发心参禅的人,首先欢迎的,可能是士大夫们。
“朱熹《答孙敬甫书》中有云:见《杲老(即大慧宗杲)与张侍郎(无垢)书》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语说向士大夫,接引后来学者。后见张公经解文字,一用此法。……但杲老之书,近见藏中印本,却无此语,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阴削去之。”
朱熹所说的是否真实,又所谓把柄是否指参话头而言,固然犹有待于研究,但大慧用儒家言语向士大夫们谈禅,则是屡见不鲜。
如他有一次用佛教哲理对张无垢谈《论语》上的“吾无隐乎尔”,张无垢初不相契,继在游山之时闻到木樨花香,大慧随口念了“吾无隐乎尔”,据说张无垢因而豁然大悟。
这一事实,不但说明大慧禅师善于用“敲门砖”,而且把“合流”的倾向扩大到佛教以外的儒家去了,似乎比他的老师又进了一步。所以《碧岩集》的版子实际上并没有毁掉,毁掉的只是某一寺院里的木板而已。
另一个例子是:《碧岩集》之后,颂古、评唱的著作很多,如宋投子义青禅师颂古、元林泉从伦禅师评唱的《空谷集》、宋天童正觉禅师颂古、元万松行秀评唱《从容庵录》等,也都非常有名。
此外如宋法应集、元普会续集的《颂古联珠通集》四十卷,汇集了四百二十六位禅师的三千多首偈颂,几乎对禅宗门下流行的公案都有了解说。元道泰编集的《禅林类聚》二十卷,把禅宗丛林里所接触得到的人物、法事和用具等等都系以历代禅师们举唱的偈颂和法语,给了丛林负责人应用上很大的方便。清代集云堂编次的《宗鉴法林》七十三卷,收集更广,方便也更多,禅师们一篇在手,头头是道,几乎可以不必参禅了,宗门自此而衰。